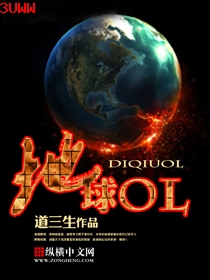甭和地球人一般见识-第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消失在染着霞光的远空中。
祈忆凌从三米多高的平房顶跳到水泥地面上,脚上穿的是基本上没有缓冲作用的塑料拖鞋,虽然全身都没有明显的伤处,但是从脚板底一直蔓延到尾骨的剧痛还是让她没有办法马上离开落地点。她原本一直保持着骄傲的笑容站在原地,丹枫这一声怒喝比腿上的痛楚还要叫她难受十倍,她的眼泪几乎是喷着出来的。
丹枫忧伤地看着她,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刚认识她的那一天。她出人意料地受伤,他却笨拙得只会质询和责问。他舔了舔嘴唇上咸涩的液体,试图平息自己的恐惧和愤怒,之后尽量温柔地问:“还能走吗?”
祈忆凌猛力摇着头,眼泪从眼眶中以奇异的角度飞出来,甚至有一滴溅到了丹枫的眼里。在丹枫的手快要碰到她的手腕时,她大力甩开了手,随后反手要用力拍回他手上,但是手最终还是停住了,她继续用力摇着头,摇一下说一个“不”字,等丹枫收回了手,才噙着泪瞪他:“不要碰我!”
已经是仲秋了,太阳在西天斜斜地挂着,阳光落在□的皮肤上居然还有点毒辣。丹枫无处可放的视线窘迫而焦虑地四处游移着,最后停在了斜对面那所房子二楼的窗檐下。那是刚才落荒而逃的小女孩的家,有一个土黄色的燕子窝干巴巴地贴在上面,等待着来年重新被叽叽喳喳的声音填满,或是被哪个冒失的孩童拿竹竿一下子捅掉。
“小七……”丹枫下意识地叫了她一声,却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春节过后就一直摆在天台里的一盆橘子在风中沙沙地响着,好像把他要说的话都吓走了。
祈忆凌没有说话,她静静地等待脸上的泪痕干透,握起双拳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自己隐隐作痛而又微微发麻的双腿,没有神采的眼睛仿佛在看着丹枫落寞的侧脸,又仿佛看到了更远的地方。
阳光的温度被地平线一点点收回了,祈忆凌终于轻轻地挪动了脚步,微微弯着腰,拖着身体朝通往客厅的门廊走去。
丹枫听到她拖沓的脚步声越变越小,听到她坐下后一把椅子咿呀作响的声音,才转身看着她走开的方向。门廊的尽头依然是这间屋子一成不变的昏暗,她没有坐在他视线所及的地方,他朝前走了一步,听到电视里传来吵吵嚷嚷的人声,停了步,转身出了门。往回家的路走时,他一路扶着身边长着稀疏青苔的红砖墙,脚步缓慢而沉重,仿佛受了严重的腿伤。甚至到了晚上,他熄灯睡下后,很快就被噩梦惊醒,于是开了灯,呆呆地看着一只小绿蚊子,它没有叮人,也没有回避光线躲到黑暗的世界里,反而乐此不疲地扮演着一只飞蛾,一下一下地往台灯上撞。
第二天他早早起来吃好早饭,到她家门前候着,却被她出门下地的母亲告知她一大早就上学去了。
他心情忐忑地走去学校,刚进校门,忽然看到昨天那个小女孩慌慌张张地跑向学前班的课室,她的身后是几个同是学前班的小女孩,其中的两个膝盖上挂着皮筋站在树下,一个站在皮筋旁大声叫着她的名字。
在小女孩离开的反方向,祈忆凌慢吞吞地走到了离皮筋四五米远的地方,歪着头看着几个正在另一棵树下跳皮筋的一年级女孩。阳光懒洋洋地落在她身上,让她的头发变成了柔和的淡黄色,隐隐泛着金光。
丹枫走过去,站在她旁边不远处的地方。聚精会神的祈忆凌没有及时发现他的到来,直到其中一个跳橡皮筋的女孩单脚立在其中的一根皮筋上久久不动看着丹枫的方向,祈忆凌才困惑地回过头来。
丹枫马上感觉血涌向了自己的耳根,他窘迫着想开口,祈忆凌却给了他一个比秋日阳光明媚热烈得多的笑容:“啊哈,枫枫!”
丹枫想回应点什么,广播体操的音乐却不失时机地响了起来。刚才还似乎显得很空荡的校园小广场上,突然间就挤满了从课室里涌出来的学生,他被人挤了一下,一晃神,祈忆凌已经不在原来站的地方了。
“回课室里坐一下也好。”他自言自语着走到一年一班的队伍前,却发现显得比以往还要羸弱的祈忆凌一脸无所谓地站在队伍的最前排。丹枫一下子懵了,他甚至想象不出她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刚才那个地方走过来的。
“……小学生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丹枫心急如焚,广播却不紧不慢地响了起来,他硬着头皮一节一节地做下去,视线一直落在他对面的祈忆凌身上。
让他大为惊诧的是,祈忆凌居然顺利地把整套广播体操做了下来,除了有部分动作显得有点生硬和做跳跃运动的时候脚尖几乎没有离地以外,就没有其他异常的地方了。甚至这两个所谓的异常,也只是在丹枫关切的目光下被放大的印象,——最起码,一向严苛的班主任站在树荫下看完了整个过程,也没有对祈忆凌提出任何意见。
反而是丹枫这个领操员因为不够专心,差点崴了脚。
广播体操与接下来的早读课以及早读课与第一节课之间都没有课间休息,丹枫坐在最后一排听得心不在焉,坐在第一排的祈忆凌在他焦急的目光下却精神抖擞,还举手回答了其他人都讲不出头绪的问题。
“你的腿怎么样了?”好不容易等到课间,丹枫把祈忆凌堵在了洗手间和教学区之间的小径上,终于问出了萦绕心头已久的问题。
“痛咯。”祈忆凌扔给他一个“这还用说”的眼神,抬脚想走。
丹枫刚才几次三番看到她走得跟个没事人似的,要不是她时不时皱着眉敲敲腿,他真要怀疑昨天发生的事是自己的梦或者幻觉了:“跳下来一定会很痛的,你不知道吗?”丹枫拧着眉看她,还有一句话忍住了没说出来:你可能会受伤,甚至—
—死。
“当然知道,”祈忆凌皱着眉朝混凝土砌就的乒乓球桌重重靠了上去,轻轻叹了一口气,“我又不是白痴。”
“知道会痛为什么还要跳?”丹枫知道她是痛得站不住了,眉心攒了起来,“你明明就是——”
祈忆凌困惑的眼神把“白痴还不承认”几个字挡了回去,她用两个手指捏着球桌沿,理所当然地说:“因为不跳的话就输了啊!”
“你已经赢了的!”丹枫别开了头。
“她说如果我够胆就跳下去跟她说,我不跳岂不是说明我是个胆小鬼?”祈忆凌依旧理直气壮。在七岁的祈忆凌眼里,真正的勇士为了胜利的荣耀是不惜牺牲生命的,她赢得伟大的胜利却只需要忍受一点脚痛,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了。——至于胜利本身的价值,她从来没有放在眼内。
这时候的祈忆凌还不知道什么叫三十六计,却早早地接受了来自它的洗礼——她年纪小小,不谙世事,对人生的苦难全无概念,却脾气暴躁又心高气傲,“激将法”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丹枫再次明白自己是拗不过她的,生平第一次“呸”了一声,又问:“你可以不做早操的啊,为什么不跟老师说你不舒服?”
“谁说我不舒服的?”祈忆凌扬起头,“如果我不做早操,那我不就输了?”
“好,真好啊,你真厉害……”丹枫接不下去了,想了想,还是不放心地问,“什么时候去看医生?”看见祈忆凌一脸茫然的样子,猜到她肯定没和父母说,于是又追问,“那你爸妈呢?为什么不告——”
“烦死了,你自己去看十万个为什么!”祈忆凌一脸不耐烦地扭开头,推了一下球桌绕开他快步走起来。
勉强用力的双脚被一阵阵剧痛充斥着,祈忆凌的额头和鼻尖隐约渗出了细汗。但是她眼神中只有些微的痛苦,更多的是恐惧和焦虑。这是一个从来不懂得危险为何物的七岁孩子心里面,对于可以随时击溃自己胜利的荣耀、扭转自己命运的大人们与生俱来的恐惧。
77、番外童年·在人间(5)
祈忆凌在林影婆娑中快速穿梭着,她火红色的上衣在树与树的空隙间一闪而过,灵活得像只初出茅庐的猎豹。她脚下不断响起干枯的枝桠被折断的劈啪声,平时走平地都会时不时被莫名其妙地绊倒的她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脚步轻快却不失稳重,就这么在蓝白蓝白的天空下一路跑进了树林的深处,径直跑向一株十多米高的招摇的柏树。
在离柏树三米开外的地方,她却突然停下了脚步。奔跑中的身体猛然被约束住,几乎要直直地往地上扑去。她左脚慌乱地朝前迈了半步,稳住了身形,脚下又响起了轻微的劈啪声,她的胸膛由于剧烈运动而急促起伏着,汗水蒸发带走热量让她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但是她抿紧了嘴唇,只从鼻子里急促而轻微地喘着气。
前方梯田的小径上渐渐现出了一辆摩托车的形状,那突突的马达声把祈忆凌低垂的眼睑拉了起来。载了满满两大筐萝卜的摩托车几乎和她擦身而过,驾驶员骂骂咧咧地从后视镜里瞪了她一眼,摩托车在路的拐角处消失了。
祈忆凌突然像被抽空了力气似的,软塌塌地蹲了下去,看着柏树的方向,眼泪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
柏树浓密的树荫下,铺了满满一层的枯叶,只有一块半米见方的土地有被翻过的痕迹,新鲜的泥土带着潮湿而寒冷的气息垒在上面,那块土地微微地拱了起来,成了个几乎难以察觉的坟墓。
祈忆凌哭够了,就站起来,拖着发麻的双腿走到坟墓处,重新蹲下,毫不犹豫地把手伸向了红褐色的泥土。正月初七,风声凌厉,冬天的树林毫无生气,鸟儿全都飞往了更南的南方,头顶脚下,只有枝枝叶叶在相互摩挲沙沙作响。祈忆凌挖着挖着突然觉得左手无名指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咝咝地吸着凉气忍着痛楚继续挖,突然感觉旁边又暗了一点,一个穿着黑色双排扣带帽毛呢大衣的男生在她旁边蹲了下来,一声不吭地帮着她开挖。
祈忆凌提起了自己的左手,拿拇指轻轻拂去覆在无名指表面的泥土。初秋的时候被镰刀割伤的那道伤口果然又裂开了,不过只是破了点表皮,之前三四毫米深的伤口内部已经基本彻底愈合。
“我口袋里有手帕,你去水库边沾点水先洗一下,等下回家再涂紫药水。”丹枫头也不抬地说。
祈忆凌没有回话,也没有拿手帕,而是把受伤的左手背在身后,右手在地上捡了根指头粗的断枝,继续挖起坑来。里三层外三层的衣服把她裹得跟个粽子似的,挖土的动作既笨拙又滑稽,丹枫停了手看着她,欲言又止片刻,也埋头挖了起来。
挖了大约一尺深的样子,祈忆凌突然一脸恐惧地握住了丹枫的手腕,眼泪又涌了出来,眼里的恐惧渐渐散去,最后变成了哀伤和哀求的混合体。
丹枫轻轻拿开了她的手,继续用双手挖着面前的土地,但动作明显放柔了。
在他挖开的泥土下,渐渐显现出了一只黑色土狗的完整形状。它身长近半米,皮毛中虽然混着众多大小不等的沙粒,但仍然柔顺整洁,甚至带有健康的光泽。尾巴毫无生气地垂在身后,几乎贴着左后腿,末端处微微地翘着,毛色是金褐色的,但仍然显得健康无比。它被埋在沙土里已经两个多小时,但仍残余着微微的体温,脸庞的线条呈现着可爱的弧度,脸颊两旁和眼睛上方的长毛不甘心地挺立着。
祈忆凌看着它,想起夏天的晚上它死皮赖脸地跟着自己打地铺的狡黠样子,无声的抽泣渐渐变成了呜咽。她伸出手轻轻碰了下它的左脸,随即触了电似地弹开,不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手,这次连背在身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