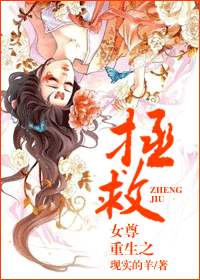十佳女(女尊)-第6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哦,这个,是安迟送来的,”我手指敲了敲盒盖,偏头打量着他的神色,见他眉头微动,像是心头不快,赶忙澄清道,“他大概是送了什么消息来了!”说着便立刻将食盒打开。
食盒共分三层,层层打开,里面一层一道菜,松子鱼、竹荪鸡汤和如意卷,可翻了个底朝天也未见到只字片语。
“你在那菜里翻翻,我来看看食盒里有没有什么机关暗门。”
容锦嘴唇抿紧,接过空盒,一边敲击辨声,一边附耳倾听,我则拿着筷子在鱼肚、点心里拨拨拣拣。
“有了!”容锦眉间一松,低声道。
原来漆红盒底的木板是活动的,只要轻轻推开,下面的夹层露了出来,那夹层不过略空些,容锦向来心细,轻而易举便找到了。
那夹层里只摆了一张薄薄的小纸片。
容锦瞟了一眼,面上的神情立刻凝重了起来,他捻起纸片,搁在了我面前,示意我看。
纸上只有潦草的四个字:“龙胎已临”。
我心中一惊,暗苦道,果然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第七十章 雪 夜
夜半时分,我缓步出了东宫宫门,只觉得心里郁郁发闷,一抬头,便看见漫天飞雪,纷纷迷迷,已在玉阶干阑上积了厚厚一层。
轻叹一口气,今日过得可不容易。
与苏幻真不欢而散,女帝有孕的消息又传来,桩桩件件都叫人寝食难安。
唯一的好事,就是我一手谋划的那件京畿营士兵杀人的事,算是得到了预期的目的。
下午将那奏折呈给陛下,陛下知晓后异常震怒,立刻下令兵部与督察院共同彻查此事,有了督察院插手,渗入京畿营,瓦解黑刀军,指日可待。
可还未等我松下眉头,转念便落到了安迟送来的消息上。
女帝有孕的事,对太女,对颜家,甚至是容家而言,都不是件小事,这弹指间,便将我们这一串人推倒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
这龙种生下来若是位皇子也就罢了,要是位公主,那太女的位置绝对保不住,而颜家和容家轻则削权夺势,重则抄家流放,毕竟愈加之罪何患无辞,对陛下而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自古以来,为了争夺皇权,父母可杀,手足可残。身为太女的妹妹若是不废不死,自己的女儿又怎么登上太女之位,女帝手中的皇权又怎能稳固?
可太女之位也不是说废就废,说立就立的,没有重大的罪责谁都动摇不了,所以一旦扣上罪名便是死罪,比如说,逆谋造反,这便要牵连无数人一起去死。
现在太女身后,还有以三部尚书为首的势力在支持着,一点风吹草动极有可能会动摇国之根本。所以眼下女帝也未将身怀龙胎的事传言出去,男女未定,必是在等候一个适合的契机。
我站在风雪之中默默出神,丝毫没有感觉到寒意,反倒越想越心惊,出了一身冷汗。
“怎么一身单薄地站在这里?”
一件狐皮坎肩搭到了我肩上,正是我之前穿的,好像刚才出门的时候落在东宫。
我转过头,发现为我披上坎肩的却是安迟。
他正扬着嘴角看着我,剑眉星眸,像是染上了一丝风雪,一身黑底红边的暗纹护卫服,外披穿一件黑色毛皮斗篷,上面积了一层斑白的雪花。
“安侍卫,真巧啊,”我回过神来,敛去了先前无措不安的表情,扯着嘴角,想随意寒暄两句就早些将他打发了,便有些敷衍地道,“自本官进宫述职以来,好似从来没遇见过安侍卫,今天倒是巧了。”
“自然不是什么巧事,是我特意来找你的,”安迟轻轻摇头,笑着对我道,边说着边为我拢了拢身上的坎肩,“否则这坎肩也不会在我手里。”
我心里觉得别扭,便不动声色地避让了过去,他见了落在领上的手指一顿,停在了半空中,一丝讪然之色在脸上转瞬即逝,眨眼间又用笑容掩饰了过去。
可他并没有收手,而是若无其事地继续为我整理坎肩,让人怀疑他是不是不懂察言观色。
“若是我一心想做成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他微微垂首,轻笑道,与那执念一般的语气不同,他脸上的表情无比柔和,理好了坎肩,他又开口道,“这个你将来便会知道。”
过刚则易折,我心里默道。
而我却与他不同,只要不触犯我的底线,我都可以放任。
“本官知道安侍卫不会无缘无故找来,”我由他摆弄去,微微错开与他的目光,蹙着眉头,低声问道,“安侍卫有什么事?”
“自然是有要事,”他抬头看了一眼凛冽的风雪,撇过头对我道,“我们去下面的亭子里说。”
我点了点头,随他一起下了玉阶,来到阶下的凉亭之中。这里有了遮挡,风雪转小,亭檐上挂着一盏小小的花灯,灯身红缨摇曳不休,烛火光亮飘忽不定,将他俊美的脸照得明眛难辨,却衬得一双眸子越发水润晶亮,像晴日夜空的星子,熠熠闪动。
我不适地转身子,凉亭外面,候在不远处的是我的轿妇,她们已将轿子上的积雪掸去,现在正抖抖索索地蹲在树下躲风避雪。
“今日早朝之后,太医院例行诊脉,女帝脉象是滑脉,胎儿不足一月,”安迟见我久久不语,率先打破了沉默,“太医院的院判、御医统统诊过,绝对错不了。”
盼了那么多年的子嗣,却是在这样非常的时候来临,不知女帝心里是怎么想的,午后见到她时,我一番察言观色,发现她似乎与平日无异,
“女帝和太后那里分别是个什么态度?”我思索了片刻问道。
“女帝大婚多年才得子嗣,自然是高兴的,虽并未太多表露,却当即让身边的贴身内侍抱霜,带了赏赐送到了凤后那里。”
我默默点头,忽然想起了一件从前道听途说来的往事,或者说那又是一出“江山情重美人轻”的悲剧。
据说女帝在还是太女的时候,曾有位情深意切的少年恋人,两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可惜那男子出生不高,做不得太女皇夫,只好勉强收做侍君。虽是如此,这两人依旧恩爱非常,便是太女娶了皇夫之后,也是独宠他一人。
雨露不均,自然后院失火。
遭到冷落的皇夫异常恼恨,一怒之下便告到了凤后那里。据说,没过多久,那侍君便消失在了东宫,任女帝几番寻觅,再多伤心,少年恋人也未再找回来。
而当时的女帝已有了半月的身孕,深受打击便小产了,她也因此落下了无法生育的病根。这事使得太后悔青了肠子,与凤后也有了隔阂。
到底百事孝为先。
女帝无法怨恨自己的父亲,便把所有的怒气都发在了凤后身上,所以,她与凤后的关系一直都是相敬如冰,若非必要绝不相睹。
恋人早已杳杳无音,生死难料,一别之后,此去经年,终有新人替旧人,凤后苦守了冷宫般的栖凤宫多年,眼下算不算是熬出了头?
有抱霜这样红人亲自送去赏赐,就已足见女帝有多重视了。
“太后那里倒是喜不自抑,不但赏赐了凤后,”安迟向我走近了一步,压低了声音在我耳边道,“太后还要陛下点封弥月大师为国师,等胎儿成了形,要她来分辨男女。”
“哦,这么说弥月炼制的丹药真的有效啰?”我转过身来,正好对上安迟低垂的脸,半盖着斗篷的帽子,半点看不出神情。
“其实,只要太后觉得有用便成了,”安迟仰起脸,轻声道,“不过陛下似乎信不过弥月,不然女帝也不会将消息隐而不发。”
这点我倒也是颇为赞同,我也正好也可趁这空档好好绸缪一番,接下来的事到底该怎么安排。
“你可有什么计划?”
他笑着问道,流光涌动照亮了他深邃的轮廓,忽然让我想起了,在荷香酒楼撞见的那幕,不由皱了皱眉头,这样不择手段地利用自己,轻贱自己,就是为了一句“没有做不成的”,是不是太功利了?
“你就非那样不可吗?”
一句话说得没有没脑,一不留神便鬼使神差地冒了出来,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想要掩饰,却还是晚了。
虽是前言不搭后语,却还是让安迟听懂了。
他将手中的佩剑握紧了几分,收回了惯常的笑颜,半饷未吱声,无悲无喜地道:“你和我不同,没挨过饿,没受过打,没被人轻视过。生我的是个高贵的身子,可我自己却是个贱种,老天这样的安排叫我如何甘心?”
原来终究是意难平。
我自出生便是世女,从来都是锦衣玉食、骄奴宠仆、香车宝马,他这样的苦头别说我没吃过,就是见也没见过。
所以我没有立场去指责他些什么,但某些后果我却是能预见到。
今天既然起了话头,我也就不怕再多说两句。
“你这样两面三刀地下去,看似处处逢源,其实哪里都得罪,哄人哄到最后,自己反倒惹祸上身?”
他抬起双眸,幽幽地看了我一眼,带着几分期许地对我道:“你是这在关心我吗?”
我听了一愣,被他这句话哽住了,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不由暗自检讨,自己为什么总会时不时地滥好人一把。
“你这样的人我是知道的,”他见我不回答,忽然勾起了嘴角,虽是在笑,眉眼之间却隐含带着几分怨怼,“你心肠软,细如针,对谁都温柔体贴。让受你体贴的人错觉你是有情,可其实呢,那不过是你的习惯,你那些示好根本就没融入自己的心进去,处处留情,却连你自己都不知,这样的多情委实比无情还要可恨!”
我闻言苦笑,心里却觉得他说得很有理。
从前,父亲为我请来的师傅,便是教我这样对待男子。
对男子尊重、守礼,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但不能过分殷勤,得若离若即,还要揣摩男子的心思,想其所想投其所好。
我学习这一切,也是为了以后能轻而易举地攻下任何一个男子的心,这样便能娶到适合颜家的夫郎了。
如今夫郎已娶,若还是这样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确有些不合适了。
“我极羡慕容锦,他是人中龙凤,风华绝艳,谋略过人”片刻他又软下声音对我道,“像他这样的男子,根本就是天之骄子,所以连你这样无心的人,也对他一往情深,不惜为他一路追到了秦州去。”
“他的确很好,”我笑了笑,想到他我心头便一片柔软,接着又正色道,“其实你也不必妄自菲薄,说道谋略,你也不见差,当初在秦州将我们耍得团团转!”
他微微摇头,不做回答,顿了片刻,又转念道:“说到他,我想起件事来,听说早上他被宣到了飞泉宫。女帝亲自过问了我和你赐婚的事,对他一番敲打,圣上口谕,要他亲自安排这桩婚事。女帝此举意在消磨他的锐气,以此惩戒你们当日为了太后懿旨,险闯宫门之事。”
女帝真是够残忍,明知他心中不愿,偏偏让他亲自操办,也难怪中午见他那般不悦,原来是这样,可他却郁郁自苦,不肯吐露。
我深锁着眉头,这样风雪连天的夜晚,我恨不得立刻奔到他的身旁。
第七十一章 窃 国
容锦刚刚担任大理寺卿,日日晚归,大多忙得比我还迟,有时甚至宿在大理寺。
我坐上轿子闭目养神,心里思量了片刻,撩起门帘,要轿妇送我去大理寺。
大理寺偏安于城东一隅,平日里十分低调地掩映草木深处,也是那些平头百姓们心中,除了大内禁宫以外,最神秘的一处。
我撩开窗帘,透过重重灰败的秃枝,依稀能看见积雪覆盖下的红墙朱门琉璃瓦,灯笼照得一切都是隐隐绰绰,风雪肆虐的冬夜,草木凋敝,困顿不堪,黑暗中的大理寺像一头匍匐休眠的兽类。
下了轿子,问过门房的仆役,容锦果然还在,早已过了三更天,他还未回去,今晚多半是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