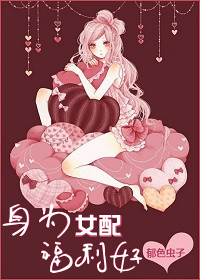指末的幸福-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可是殷凌的嘴巴好像上了锁,还是银行钱库级别的金刚锁,任童撤想尽办法都撬不开来。无奈之余,她只好杀向了正在美国努力上进的罪魁祸首。
在这个世界上,若有人能封住殷凌的口,那除宫煜外,童撤不作第二人想:“说!你给我说!”
宫煜在视频那头看她气鼓鼓的模样,差点笑喷:“小朋友,你到底在殷殷那里受到了多大的打击?至于这样么?”
“我呸,你才是!我家殷殷一向对我开诚布公,不留秘密,你到底给她下了什么蛊,搞得她跟个铁蚌似的!”
“我像这种人么?”
“像、极、了!”
“啊,小朋友,我的心受伤了……”
“少给我耍宝,你已经年老色衰了,别再想用美色转移话题。”啧,老虎不发威,还真当她是Hello kitty了,“你不说就别怪我就加入萧珞的阵营,老实说那小子为殷殷做了很多,老娘也不是不感动的!”
宫煜闻言沉默了一会,还是那副嬉皮笑脸的模样,但已不再出言搪塞了:“童童,我和殷殷之间没那么简单,我也不知该从何说起。这样吧,我答应你,等你结婚那天,我一定当面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希望你大人大量,至少站个中立,千万别在后院放火!”
童撤虽不甚明白,但至少知道了他的态度,这一次他是真的出手了:“真是的,早干嘛去了?”
别人怎样她是不知道拉,但宫煜这个没良心的家伙,相信就算有人快死在他面前了,他也只会冷冷看一眼,顶多帮忙打个120。
他这样自私自利的家伙,绝不会犯萧珞那样的错。
宫煜苦笑:“若不是有难言之隐,我又何尝愿意如此……”
童撤听了直翻白眼:“靠,你要现在不交代,就别再折腾我可怜的好奇心了!它很脆弱的!”
宫煜还是笑,不过这一次没了那抹淡淡的忧郁,反而多了些戏谑:“听说你和傅奕好事将近。”
“消息怪灵通的啊!看来你和殷殷比我想象得联系得多。”
“那倒不是。只是殷殷说若你们决定无视长辈结婚,那我不管怎样都要回来参加婚礼。”
“哈哈,够朋友。那你会来么?”
“我哪敢不来?这不是和你讨饶来了么,麻烦你们不管怎么猴急,至少熬过这两个月,等我毕业啊!现在我忙得翻天覆地的,连睡觉都没时间,哪还敢奢想回国啊!”
“放心啦,我看最少也得半年,傅奕还有年底才满22岁,何况如果可以的话,我真不想搞什么私奔。”
“别想太多了,姐弟恋很时尚啊,有什么不好的?卢克?沃洛不都和凯莉?奥斯本都要奉子成婚了么?”
“呦,你还挺八卦!”童撤被他逗笑了,这段日子她过得很累。父母果然无法谅解她的感情,而她一向孝顺,这次违逆他们,心里自然不好受。
“我关心一切美好的姐弟恋。”宫煜若有所指地说道,“虽然我不太欣赏傅奕那小子,但若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我会尽全力的。”
“谢谢你,宫煜。”童撤真诚地说道,对现在的她而言,每一份支持都很重要,都能给她坚持下去的勇气。
********************************************************************************
心理学上有种现象叫“朱丽叶和罗密欧效应”:当相恋的男女当遇到外界的阻力时,反而会促成他们的姻缘。越是受到外界的阻力,比如双方家长的强烈反对,越是能加深恋人之间的感情。
童撤和傅奕显然就是如此,虽然他们遭到了几乎所有长辈的反对,可在一起的决心却不曾改变,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坚定。
他们一边和家里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一边努力找寻着自己的出路——经济独立。
在苏樱和萧珞的帮助下,童撤很快掌握了面试的技巧,在杭州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率先独立起来。
而傅奕原本就有份兼职,虽赚的不多,但凭借多年积蓄也算可以维生,甚至可以偶尔小小的滋润一下。
他们在市区内租了间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距离童撤上班和傅奕上学的地方都不远,小日子过得不算富足,倒也不缺什么。
在此期间,苏澜曾回到杭州看望了殷凌一次,对她好吃懒做、毫无规律的生活很是不满,不顾殷凌的阻拦迅速活动起来。她很快通过关系,将殷凌弄进了本地一家报社当记者。
殷凌的简历原本就很出彩,名校毕业成绩上佳自然有不错的学习能力,缺得只是些经验,耗点时间做点活儿,很快就能上手,所以不难讨到岗位。
何况,她还非常耐得出贫穷——拿的是杭州市人民最低工资。
可尽管薪水微薄,工作任务却意外的繁重,几乎日日加班到九十点钟,节假日也成了工作日,忙得她是焦头烂额,并且一度时间成了有名的失约达人——
常常玩了一半,就被上司一个紧急电话强行拐回到单位。
殷凌的直属上司是个精明的中年人,很知道要如何物尽其用,看准了殷凌内心懒得反抗的本质,不但把她当小妹使唤来使唤去,还在知道她的英文能力出众后,把大量翻译的活儿全部无偿交给了她——彻底免费地使用着殷凌的所有才能。
虽然大家都刚开始新生活,没有谁比谁空闲,但若比及殷凌,倒也都还轻松。萧珞即便想约她都没那个机会。
童撤对此事的评价是——“小狐狸,狡猾狡猾滴,我看他根本是指派他老妈上来看守领土的!”
当然,这其中还有她个人的怨恨。因为她经济拮据,所以没有本钱当甩手掌柜,婚礼置办什么的都得靠自己。
而殷凌又老爽约,搞得童撤一个人忙得焦头烂额,连着心情都差了好多,可怜无辜的傅奕每天面对悍妻,日子跟着不好过。
他只是非常心疼她,因为童撤有的不是忙碌,还有巨大的精神压力——刚开始工作的她,不仅有介绍人的人情债,还有为了和傅奕在一起不能失去工作的经济压力,再加上她资历浅总有比较多的杂事要处理,又有很多学校不教的东西要学习,所以比任何人都辛苦,还要强撑着和同事处理好人事关系,为此每天都早半小时到办公室搞卫生。
如果说殷凌是忙碌,那童撤就是疲惫,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疲惫。好几次她都突然腿部发虚,差点摔倒。
为了调整身体状况,她平日回家基本是不太作家务的,尽量堆在一起到休息日一起做,所以有空的时间本就不怎么多,好容易约了人帮忙还被放鸽子,她能不怨恨么?
童撤现在对殷凌上司的恨意已飙升至定点,天天晚上拿这秃头的名字作射飞镖的靶子,做饭后运动。
当然她的饭后运动很丰富,还有洗碗擦桌子抹地板。不是傅奕懒惰不愿意为她分担家务,而是他也忙,又要上学又要打工,往往吃完饭就要往外赶。
但不管多忙多赶,他都坚持要回来陪童撤吃晚饭,若真来不及就叫她一起在他打工附近的餐厅吃,这是他们的家庭情趣。
童撤也直到这会儿才相信:这个孩子为了和她在一起,真的是数年如一日的拼命。心里一感动……犯了女人都会犯的错,居然咬着牙把大半家务都承担下来。
苏樱和殷凌知道后,倒是默契十足地意见一致:“这女人啊,不负传说的恋爱傻子!”
可是,却不是不羡慕的。
因为能让大女人心态的童撤,心甘情愿洗手作羹汤的理由只会有一个——对方对她更是十倍的好。
任谁都没想到,外表妖孽并倍受女生欢迎的傅奕大帅哥,居然如此专情并且长情,几年如一日地守候着这段恋情的逃兵,宁愿抛弃自尊也不肯放手。
看他们这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饶是对感情有些绝望的殷凌,也忍不住被他们这份纯挚打动,于是一边打着中立的旗号,一边默默为他们铺路。
殷凌有时候会想,或许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感情存在,她才能继续相信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相信总能绵延得长久,却偏偏不能坚持到底。
当日子已经趋于平静的时候,总会发生一些什么,来颠覆人的信仰。
一次又一次,就好像命运正带着讥讽的冷笑,无情地俯视着世人的挣扎沉沦——
两个月后的某个周六下午,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炸得殷凌一阵头晕:“童撤被车撞了?重伤……?昏迷……?在哪家医院,我马上……什么?不可能!你胡说!”
殷凌反射性地尖叫着,顾不得同在加班的同事们诧异的目光,惨白了整张脸:不,这怎么可能!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苏姐一定是在开玩笑,童童明明下个礼拜就要结婚了的,苏姐怎么可以开这样的玩笑!
“殷殷,童童……她真的死了。医生说送到的时候已经晚了。”苏樱看着走廊上来来往往疾步匆匆的人,轻轻抬起下巴,却止不住那如雨的落泪。
她的身后是一张雪白的床铺,上面还带着一点点腥红的颜色。
“不,我不相信……”殷凌跌坐回椅子上,像被什么哽住了喉咙般,反反复复说着这四个字,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强调自己的立场,可落在桌面上的泪珠却一滴接着一滴,仿佛在嘲讽她的虚弱无力。
殷凌当然知道苏樱决计不用会用这种事开玩笑,可是她怎么可以相信?
几个小时之前,童撤还带着大包小包的零食出现在她面前,一边帮她打下手,一边愤愤地替她抱怨她那位永远不记得员工权利的上司,并因为自己调侃她显然去约会的漂亮装扮而羞红了脸。
她们还一起为半个月后那场小型却浪漫的婚礼做了很多计划,有缤纷美好的玫瑰花雨,也有诱人至极的巧克力大餐,然后童撤会穿上不很昂贵但是非常精致漂亮的白色婚纱,和傅奕交换誓约的戒指,成就又一个童话般美丽的恋情。
殷凌还那样清楚的记得,童撤那时笑得好甜好灿烂,一直甜到了她心底干涸已久的地方。
可为什么不过才那么一点点的时间,这个梦幻般的婚礼就真的要变成一个梦了呢?
她真的不懂。
殷凌坐在由于空调功率过大而闷热异常的办公室内,只觉全身发冷。
她一定是在做梦,一场荒诞的可笑的噩梦。
年三十到了,大家过个好年呦,多拿点压岁钱,多吃点好吃的!
减肥什么的事儿就等年后再说,相信大家都会漂漂亮亮、开开心心!!!
48
48、噩梦降临 。。。
殷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去的医院,也不记得是如何找到准备的病房,脑子里空空的,好像被什么刨了一个大洞,听得见风在内里穿梭,摩擦着血肉,戳刺似的疼痛。
她其实到的很晚,闻讯而来的人早已将小小的房间围得水泄不通。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不敢置信的凄惶表情,可殷凌全都看不见。她笔直地朝他们中间那隐隐若现的白走去,期间不断有人上前拍着殷凌的肩膀以示安抚,还有人握住她冰凉的手,想要给她一些勇气和温度,可是她却麻木得没有任何感情。
殷凌想那应该都是平日里和自己非常亲密的朋友,可她却怎么也看不清他们任何一个的样貌。
她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明明心在尖叫着说想要逃离,人却还是摇摇晃晃的,一步、一步地走向那张除了白还是白色的床。
空气中漂离着死亡的气息,静谧的、熟悉得让她全身颤抖。
她还记得很多年前的那个冬天,也在这样一个类似的房间里,不管她怎么哭叫哀求,妈妈还是躺在一张类似的病床上,带着满心的遗憾和不舍永远地离开了她。
她也还记得四年前那个夏天,同样刺鼻的消毒药水味,刺激着她紧绷的神经,逼迫她接受自己已经失去孩子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