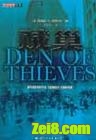刺客千金贼-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柏氿猛地一羞,探起头便想要朝那些吃瓜将士们飞几个冷飕飕的眼刀过去。
她还没来得及伸长脖子,便被殷瑢按着脑袋压在他胸前。
柏氿撇撇嘴,却乖乖的没再动弹。
男人的面子比天大,他要在手下面前呈呈威风,她由着也无妨,正好还省了她回营帐的这几步路。
殷瑢抱着柏氿进了主帐,转个弯便朝帐里的床榻走去。
他将她放到这床榻上,俯身便压下来。柏氿眼见着他越靠越近,突然伸手勾住他的脖子,一个翻身将他压在自己的身下,完了又一把扯开他的衣襟。
殷瑢七分惊喜三分惊诧的挑了挑眉,风情万种的躺在她身下道:“夫人,你这是终于把持不住要将为夫收入帐下吃干抹净从此夜夜颠鸾倒凤巫山云……”
柏氿没让他把话说完,便在他嘴巴里塞了团手帕。
殷瑢的眉梢跳了跳,他正要把嘴巴里的手帕拿出来,才伸手,却被柏氿按住。
柏氿捉着他的两只手腕按在他的头顶,又扯他的腰带将他的手腕绑了起来,吊在了床檐上……
殷世子难得有点不淡定不从容了,但却也不挣扎不反抗。他深而沉的看着她,像是在问,你要做什么?
柏氿咧了咧嘴巴,取过一只蜡烛,阴测测的笑道:“滴蜡。”
见她这般装模作样装神弄鬼,殷瑢反倒了然了,索性也就乖乖的躺着,任她鱼肉。
柏氿点燃蜡烛,将医用的解剖刀放在烛火上烤了烤,确定消了毒才俯下身去,细细割掉他箭伤上的微微开始化脓的皮肉。她当了许多年的刺客,时不时便会受点小伤小痛,处理这样的皮肉伤,绰绰有余。
柏氿俯着身,靠近这片伤口,她的长发从肩头披散下来,发梢抚在他的胸膛,细细的痒。这微微的触感却掩盖住那刀割的疼痛,一点一点在心头燃起幽幽的火,足可焚身。
殷瑢忽然咬紧了帕子,握住了拳,额角渐渐沁出一层薄薄的汗。
柏氿只以为他是疼得受不住,于是她便在他的伤口上轻轻吹了吹。
一息清浅,如天鹅的羽毛挠在心尖。
殷瑢的眸光微微一暗,像是薄云遮了远山,山雨欲来。
柏氿没发现他这一刻的暗潮涌动,割完他伤口上的腐肉,便解开了绑着他手腕的腰带,让他坐起来。
她从药箱里取出绑带和伤药,正要给他包扎,殷瑢却突然扯过她的手臂,翻身一压把她压在身下。动作间,她手里的纱布绑带跌落在床边,滚出一道长长的白线。
殷瑢压着她的手腕,又扯过纱布在她的手腕上迅速绕几圈,绑起来,吊上床檐……
柏氿一僵,未及反应,他便俯下来咬住她的脖子,细细的吮吸着烙下一颗颗红印。
柏氿偏头要躲,“我身上脏……”
他却抚上她的侧脸,扳过她的脑袋,断了她躲避的后路,一边继续咬,一边含糊的道:“不嫌弃。”
他这样贴着她,心头那片箭伤还淌着血,这血晕开在她月白的衣袍上,越发嫣红如那盛开在枝头的血梅花。
柏氿目光微颤,声音莫名便有些不稳:“你流血了……”
殷瑢从她的脖子一路咬上她的锁骨,伸出手来摸索着便要去解她的腰带,“不碍事。”
他解了她的腰带,扯到一旁,动作间却又有鲜血溅出来,洒在她微散的衣襟上,这一幕太过血腥,柏氿看得心里一疼,眼底又升起些微的涩意。
“殷瑢,”她微叹着低低的唤,“别这样……”
殷瑢一顿,停了动作,复又不甘心的咬了咬她的耳垂。
柏氿痒得一缩,他又腻过来,不肯轻易放过她,慌乱间,她听见她自己说:“那种事情等你的伤好了再……”
一语未尽,她自己先住了口,咬着下唇噌的涨红了脸。
殷瑢闻言,从她耳侧离开,撑起身体自上而下的看着她,挑了挑眉,像是一只猎豹抓到了猎物的弱点,便死死咬着绝不松口。
“等我好了,再……嗯?”
他这尾音太过于调侃而玩味,听得柏氿三分怒,七分羞,又羞又恼间只想快点把这事翻过去,给他上药包扎。
于是她胡乱的点了点头,又道:“上药要紧,你……”
那一句“你放开我”还没说完,殷瑢便已松了手,解了她手腕上的绑带,又把纱布和伤药塞进她手里,无比乖巧而积极的等着她上药,大约是觉得越早养好伤,便能越早脱单**撒狗粮。
越早越好,力争分秒。
柏氿看着他如此眼巴巴的等待,好像一只正襟危坐的犬类动物,闪烁着那亮晶晶的眼睛,无比温顺的期待着主人摸摸头顺顺毛再揉一揉它的肚皮。
他本该是那样一个尊贵孤傲而又妖孽的人物,何曾想,他竟也能有这样一副忠犬的模样。
柏氿不由便笑了笑,很淡,却是难得笑入了眼底。这笑容如昙花一现,一绽方歇,殷瑢突然伸出手来抬起她的下巴,定定的看着她。
“怎么了?”柏氿奇怪道。
“珍藏。”
这个回答颇为古怪,柏氿想不明白,索性便由着他去。
深夜,军营里的烛火闪烁着跳动。
柏氿为殷瑢系好绑带的结,正要收手,却被他抓在掌心里,向上摊开。
烛火的光芒倾斜着照在她的手心,她的手心里有一片被碎石扎破的伤。
“摔跤了?”殷瑢问。
许是他的音调太沉,能够摄人心魄,又许是他的目光太深,一眼便能看穿她那样焦急的夜奔,又那样不顾一切的扑在血泊里。
柏氿忽然微微红了脸,直觉便想抽回自己的爪子,“不是什么大事。”
殷瑢却没让她得逞。他取了镊子一点一点取掉她伤口里的细碎沙石,又作势要拿过纱布上药包扎。
柏氿连忙收回自己的爪子,背到身后,“一点小伤而已,没这么严重。”
于是殷瑢便住了手。他在暖光的烛光里深而远的看着她,半晌,忽然又牵过她的手来。柏氿以为他执意要给她上药,便微微挣扎起来,“真的不用……”
话音未落,却见他俯身在她的掌心里吻了吻。她掌心伤口里的血染上他微薄的唇,像那苍蓝的夜色之下,有风将枝头血梅的花瓣拂落在雪地上,触目,惊艳。
柏氿被这艳景惊得微微一怔,怔愣间便已被他拉进怀里。
她在他的胸前数着他的心跳,第一百八十六次心跳过后,他在她头顶上方道:“柏氿,等此间事了,我们回了泽国,便再成一次亲吧。我再娶你一次,不是殷世子和宁家小姐,”说着,他顿了顿,微微抬起她的下巴,自上而下望着她,沉沉道:
“而是泽国的王,和他的王后。”
☆、第101章 犹记当初年少时
夜色山谷,山谷笼在弧圆繁盛的星空之下。星空之下有人在山谷里燃起一簇簇篝火,篝火跳动着焚烧谷中无处安放的,将士的尸体。
血肉成灰随着幽幽夜风荡到天上,白骨化泥携着点点火花落在地里。
风,呜呜而鸣;火,曳曳随风。
军营的夜,死寂深凉。
浩大的深凉里,忽有一声骄纵的厉喝响彻夜空:“你们就给老子吃这玩意儿?!是不是想死!叫你们的主子来见老子!”
公孙城猛地砸掉手里那一碗稀粥,怒气冲冲的便想冲出营帐。
营帐外一左一右的两个守卫兵伸出手里未出鞘的刀,交错挡在营帐口。公孙城一头撞在这两把刀上,顿时撞得头晕眼花。守卫兵又齐齐将他往营帐里一推,他被推得后退几步,一时间站不稳竟是一屁股摔在地上。
眼前的晕眩尚未退去,心底的暴怒已然升起。公孙城噌的站起来,赫然抬手指着帐外的守卫兵便要破口大骂。
恶毒的谩骂还没有出口,他却突然一顿,僵硬得连那伸在半空的手臂都忘了放下。
帐外,有篝火裹着残肢白骨张扬跳跃,有落叶随着暗夜晚风纵身扑火。有人负手站在树下火边,明黄的火光映照他一身青衣飘飘,飘在微凉的夜风里,像那烟雨蒙蒙的灰白狭道上,一人负剑迎风而行。
沉静,内敛,寂寥苍苍。
公孙城脸色微白,眼底又似有水光微晃。他怔愣片刻,片刻之后又突然更加凶狠的朝营帐外面冲过去。
帐外的守卫兵面无表情伸手一挡,他便又一次跌了回去,跌在泥地上,手掌磕在地上碎石,擦破了皮,流出了血,渗进地里。他这锦衣玉食的半辈子里还没受过比这更严重的伤,但他却看也不看自己的手掌一眼,咬咬牙爬起来又埋头冲出去。
守卫兵第三次把他挡回去。公孙城的额头撞在刀鞘的边角上,磕出了血,血水细细长长从额角流下,流过眼角,带出一汩透明的水花。
……男儿有泪不轻弹,阿城,老子跟萧策都没哭,你嚎啕个啥?
有年少稚嫩的嗓音回响在耳畔,如此之近,像那抬头便可看见的天上白云;如此遥远,任他奋力登山追赶,云,依旧在他的头顶,目之所见,触之不及。
公孙城的指尖深深抠进泥地里,指甲盖翻了起来,扎进肉里,疼在心底,又逼出眼底的水花。他死死咬着下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咬得出了血,也不松口。
他曾经是那样一个纨绔子弟,声色犬马浪荡成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不与自己过不去。如今却不知为何突然发了狠。公孙城握着拳,携着一身的伤和土,从地上一点一点爬起来,不管不顾的又一次朝帐口扑过去。
守卫兵伸手一挡,却被他紧紧的扒住了手臂。他用那掀翻了指甲盖的手指死死揪住守卫兵的衣袖,血水从指尖的伤口里爆出来,眼里的泪花跟着血水一起迸出来,却不是因为疼。
夜,深而凉;人,癫而狂。
公孙城几近执狂的扒着守卫兵的手臂,直朝帐外那人喊:“萧策!萧策!是不是你?”
他如此狼狈而癫狂,树下那青衣的人似是终于动了容,挥手退下帐外的守卫兵。
一直死死拦着他的守卫兵当即撤下手臂,公孙城一时没了对抗的力道,顿时向前摔在地上。
他却没觉得狼狈丢脸,不等自己爬起来站稳身体,便又连摔带跌的朝那人跑过去。
他跑得太急,左脚绊到右脚扑通一下便摔了个狗啃泥,有一朵泪花溅落在草尖,碎裂成点点星芒。他忍痛撑起身体,泪眼模糊中看见眼前一双薄底黑靴。
公孙城一怔,缓缓抬头。
于是他看见他衣袍翻飞如碧玉流水;看见他脊梁挺拔似月下苍松;看见他眉目冷峻,像那料峭远山,在暗夜风雪里岿然不动。
暗夜,微风凉凉。
他趴在地上自下而上呆呆的望着他。
他站在树下居高临下面无表情的看着他。
一上一下对望一刹,有回忆如血雨腥风携来巨浪惊天而起。
犹记当初正年少,年少不识愁滋味。
许宣王十三年,初春。
这一年的春天,宫里的学堂多了位王子伴读。听说这位伴读的父亲在朝里官职不算大,却与萧家的萧风大司寇沾了些亲故,所以才能送入宫上学来。
那位伴读年纪不过四五岁的样子,长得白白净净,却不与人来往,沉默寡言孤僻得很。
这样没有背景却又不懂变通的学生,在学堂里,最容易受到别家子弟的欺负。
那伴读平日里受了言语欺侮,也不吭气,沉默得像块石头。于是,以邢子真和朱宇达为首的纨绔子弟便欺负得越发起劲。
直到有一天,邢子真抢了他手里的一支簪花,踩在脚底下调笑:“你怎么会有这种小娘子的玩意儿?莫不是个娘娘腔?”
那天,那小小的伴读终于动了怒,瞪着眼睛,一拳朝邢子真砸过去:“那是我要送给我妹妹的!赔我!”
邢子真挨了他一拳,当下也发了火,喊上周围的孩子便要群殴。
就在这时,一旁的草丛里突然传来一道声音,明朗如那天上的阳光。
有一个小男孩枕着手臂躺在草地里,晒着太阳,嘴里还叼着一根不知道从哪里拔来的草,“邢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