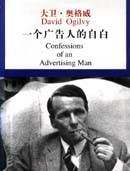一个叫阿树的女人决定去死-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什么报应!”
程树张了张口。
她想说,她已经得到报应了。
但是她没能说出口。
在她的生活里,陈北及的事已经是一根致命的□□,随时会将她炸入万劫不复之地;而郭简灵的话就像一连串的荆棘,每日每夜地刺痛着她的神经,将她拉入更深的沼泽地。
她完全可以不接郭简灵的电话。但是她没有。
这像是一种自虐的方式。郭简灵的话如影随形,随时随地得告诉着她,她做了什么错事,又将因此会怎样陷入这种无穷无尽的悔恨与自责中。
电话那头的郭简灵边哭边骂:“我早就和小北说了,叫他别和你在一起。他就是不听话,他就是不听妈妈的话……程树,你为什么要缠着他,你为什么缠着他……!”
爱情是一种原罪吗。程树想。
她恍恍惚惚地陷入了自己的沉思,耳畔全是郭简灵的啜泣声与咒骂声。
似乎过了很久很久,那边的电话突然被抢下,随之而来响起的,是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
“程小姐你好。”他自我介绍道,“我是陈钦。”
程树顿了顿,终于开口:“你好。”
陈钦——她从陈北及的口中听过这个名字。
这是陈北及堂哥,他大伯的儿子。
自从陈北及的大伯和伯母在二十多年前出车祸身亡后,他的爸爸便把陈钦领养到自己名下,让陈北及和陈钦成了名义上的亲兄弟。
从前,程树听陈北及提起他这个哥哥,都是“我哥”、“阿钦”这样,叫得十分亲密。
她知道他一向很敬重自己的这个哥哥。自从陈北及撂了家族摊子一走了之,一门心思搞艺术之后,就是他的这个哥哥在撑着家族生意的场面。
陈钦的声音浑浓,很难让人走神:“程小姐,我小婶她最近因为北及出了事,精神很恍惚。我刚刚才发现,她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给你打了很多个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觉得北及的死是你的错,但我明白,这件事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大可不必将她的话放在心上,我也郑重向你道歉,只是……”
他欲言又止。
程树抓着手机的指尖紧了紧。
陈钦见她没反应,继续道:“只是,关于北及的追悼会……我希望程小姐你还是不必出现了。”
他话说完的那一刻,程树的思路一下子飘远了。
她想起她和陈北及刚认识那会儿,是在一个独立纪录片的放映会上。
那天的片子叫《骨未成灰》,讲得是重庆的一家养老医院里的事,她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们一个个佝偻着背,目光浑浊,行动迟缓,就算隔着屏幕也能闻到他们身上独属于死亡恶腐朽气息。
影片最后的半个小时里,她一直在哭。还是邻座的男人给她递了一张纸:“擦擦眼泪吧。”
“谢谢。”她转头看了他一眼。
他的头发有点长,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个尖锐的下巴,印满粗粝而犷然的细碎胡茬。
等放映结束后,有人拿着话筒站起身来高谈阔论着自己对于医疗、养老、保险系统的见解与批评,男人却转过头,没头没脑地冲她说了句:“还有二十九年三个月零六天,我一定不在这个世上了。”
“为什么?”她愣了好一会儿。
“那时候我都60岁了。”男人叹了口气,一指屏幕,一本正经道,“你看看他们,老去多恐怖啊。我可不能容忍我活在一个再也没有姑娘为我疯狂的年纪。”
这回程树看清楚了他的脸。
这人是很帅。她想,一时没忍住,轻笑了一声。
“活60年就够了?”
“够了。”男人点点头,“最好不要自杀,天灾人祸的就很ok啊。自杀之前要做的心理建设太多了。”
他的脸在灯下烙下深深的阴影。程树觉得有些恍惚,一下子愣住了。
从小到大,她也无数次地想到过“死”。
她不是没有想过自杀,可是相比车祸、疾病甚至谋杀,自杀会让她背负太多的心理负担。
她也从来不敢和别人说自己的想法。有时候走在街上,她恨不得那辆公交车突然失控撞死自己,可是一切井然有序,她也从不曾和人提起。
没想到,有一天,有一个人在她面前坦坦荡荡地说了这件事。
没有隐瞒,没有矫饰,而他们都是互相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程树第一次知道,死亡这件事,也可以被自然地谈论起——
坦诚、平常,甚至可以带上些黑色幽默的风趣。
那时候的程树已经很多年没有爱上一个人。可是她确信,自己在这一瞬间爱上了陈北及。
当时她想,这男人真有趣,如果自己能去参加他六十岁的追悼会就好了。
骨未成灰。骨未成灰。眼下,一切物是人非。离那个终点还有一半的旅程,他就死了。
而且,她还不被允许参加他的追悼会。
程树努力将自己的思绪拉回来,然后又努力找回自己的声音。
“好的。”
她没有说多余的话。
陈钦的声音里带了一丝欣慰:“那么你保重,程小姐。”
“谢谢。”
陈钦挂了电话。
程树仰躺在床上,全身脱力,大汗淋漓,动弹不得。
这真是个荒谬的世界啊。她甚至连苦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过了很久很久,程树才慢慢地翻了一个身。然后用力地伸出手,抓起床头柜上的六片安眠药,径自吞了下去。
她躺回床上,轻轻闭上眼睛。
希望今晚能睡着。
希望今晚不再梦见他。
陈北及。
意识模糊前的那一刻,程树的脑中莫名其妙地涌现了隔壁男人的那张脸。
她想——他和陈北及到底是不一样的。
如果,今天下午在平台上看到自己要自杀的人是陈北及,他宁可和自己一起跳下去,也不会像那个男人一样,花费那么多的口舌来说服自己好好活着。
可是,她自己都没想到的是。
她竟然被他说服了。
☆、疏离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胡一民就起床开门。今天杜宜美要坐早班车去赶飞机,耽误不得。
结果,杜宜美还没下来,谭临倒先下来了。
“哎,阿临,早啊!”看到他,胡一民打了个招呼,“怎么今天起的这么早?”
“我要回家一趟。”谭临说,“临时出了点事。”
“啊?回去一趟?”胡一民看向他的身后,“你不带行李走?这么突然?”
“嗯。”谭临点点头,“过几天吧,我还要回来的。”
胡一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
“房费照付。”谭临加上一句。
胡一民在心里嘀咕:这年头,怎么一个两个的都这么有钱?先是那个程树,一住就是一个月,房费源源不断地付着,也没见她做什么有意义的事——
这个谭临么,更奇葩了,都回去了行李还不带走,还说要再回来,还要付空房间的钱?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窗外。
这地方是有什么金银财宝哟,大家都舍不得走了?
两个人正说着话,楼梯上一阵“咚咚咚咚”声,杜宜美又蹦蹦跳跳下来了。
她一看见谭临,一张脸便冷了下来,看都不看他,也不和他说话。
不过,她很快就破功了。等听到胡一民和谭临聊什么“你这次回去,哪天再回来”的话,她终于忍不住,一下子凑了过来。
“阿临,你要走啊?”
“嗯。”
“那我们是坐一班车走咯?”杜宜美笑得眼睛弯弯。
“是的吧。”
“那太好了!”杜宜美一拍手,“待会儿你就换个座位,我们俩正好坐一起,路上有个照应,你说是不是呀?”
正在此时,楼梯上响起一阵极轻的脚步声。谭临没回答杜宜美,转头向楼梯方向看去。
是他最先看到从楼上走下来的女人,然后是胡一民。
下一秒,胡一民就惊讶地喊了一声:“阿树!”
从前,这女人要么已经在平台上抽了一夜的烟,要么一直等到晚饭时候出来晃一下,从来不会在一个这么正常的时间点下来啊!
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么热闹?
他心里这么想着,乐呵呵地招呼了一声:“阿树,他俩等会儿就要走了,一起吃个早饭呗!”
程树的目光投过来。
她的眼神从谭临的头上极轻得掠过,声音近乎呓语:“走。?”
谭临说:“家里出了点事,要赶回去。”
程树微一点头。今天她又用那支笔把头发盘在脑后,凌乱稀疏,愈发衬得她下巴下的两条锁骨尖锐而瘠薄。
她光着脚,走到桌子前面坐下,盛了一点粥。
胡一民问她:“今天是要出去吗,阿树?”
程树点点头。
“要开始工作啦?去拍东西?”
“嗯。”
胡一民一听,连忙热心肠地提议道:“前两天你都没怎么吃东西,往上爬去金坑瑶寨那边可能吃不消。要么今天么,你就往下走,到平安壮寨那边,又近,也挺有味道的!”
他乐呵呵地给程树拿了一个鸡蛋,又道:“不过么,你也知道,现在这种古城啊古村啊的景区里头都差不多!瑶寨那边还好点噢——壮寨更靠山脚,商业气息就浓了!我看你们这样的艺术家,估计也拍不到什么想拍的东西……”
“谢谢。”程树放下筷子,“走了。”
“啊!?”胡一民没想到,就自己唠叨了几句话的功夫,程树竟然把早饭吃好了。他转过身来再定睛一看,对方只喝了点稀薄的粥,那个鸡蛋碰都没碰。
在他愣神的工夫里,程树已经站起身来,往门外走去。
“哎哎哎!”胡一民试图叫住她,“就吃那么一点怎么行!”
她前两天都没有好好吃饭,今天只吃了两口粥就要出门爬山——壮年的小伙子都有点吃力,更何况这个女人这种风一吹就要吹走的模样!要是晕在哪个犄角旮旯,他怎么找得回来?!
此时,谭临也放下了筷子。一旁,只余杜宜美一人咬着一只肉包,吃得津津有味。
门口的程树回了极轻的两个字,胡一民根本没听清。他只焦急得往前走了几步,就想拉住她。
“我和她一起下去吧。”沉默的男人突然开口。他站起身,“反正顺路,不是吗。”
谭临自告奋勇与这个怪里怪气的女人同行,胡一民自然求之不得。他就怕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出了事,既然现在有人把这个风险承担了过去,他顺水推舟答应下来。
“哎!好嘞!阿临你和她走我就放心了!”
他的话音未落,身后的饭桌上就骤起一声“砰!”的响声。
胡一民吓了一跳,连忙转头去看——
饭桌上,杜宜美一口气把白粥喝完,然后把碗甩在了桌上。
“哎哟,小美啊,你……”
胡一民急吼吼地上前,将倒扣在桌上的碗翻了过来。
现在的小姑娘都这么恐怖吗,感情受挫跟他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拿他的碗撒气?
杜宜美冲他一笑:“不好意思啊,一民哥,手滑了一下。”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红彤彤的钱,“喏,这两天玩得很开心,谢谢你啊一民哥。”
胡一民愣了愣,客气了一下:“小美,大家都是朋友,你也不用这样……”
“一民哥,你这客栈开在这里,也挺不容易的。”杜宜美边起身边道,“这是我的谢意,你就收下吧。”
说完,她没等胡一民再客气一下,就大踏步往外走,跟上门外的谭临。
门外,程树已经走下了台阶,身影完全消失。谭临紧随其后,然后是杜宜美。
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客栈一楼,瞬时间门庭冷清。
胡一民想着这怪异的三人组合。然后,他轻轻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真是年轻啊。”
*
这一路上,谭临走得颇不舒服。
先不说杜宜美一直在他身边搭讪,叽叽喳喳地找话题聊天;就说程树,一路都走在他前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都没转过头来看过他一眼,更别提来两句正常的交际了。
这让谭临一直处在一种矛盾而极端的处境中。
他向来知道他是个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人。
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