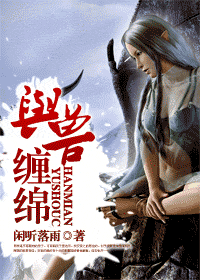或者缠绵,或者诀别-第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安谙,枉我说我理解老巴赫热爱老巴赫,要到此刻我才在这些音符里读懂音符下面隐藏着的缱绻深情。一如你当年予以我的每一分关怀。
如果这都不算爱,还有什么算是爱。
可是到我明白爱的时候,爱已不可能。
车忽然停下。我使劲用衣袖揩干脸颊上的泪。再抬头看见安谙拉开储物箱正在翻找东西。很快他找出一盒药,仔细看了看,下车,打开后车门,扶起我道,“刚过保质期。应该没什么事。先吃着吧。没看见有药店。前面上高速,更不能有药店了。”我看一眼药,熟悉的包装熟悉的牌子,与三年前我去广州时他备在我包里的一样。安谙,这是你一直为我准备的么?你怕我回来后不知什么时候胃痛为我准备的么?你在三年前就为我准备的么?可我已不再能够流泪。因为小诺正在回头看着我。
他按挤出一粒药,放在掌心递到我嘴边,就像以往他每次喂我吃药一样,可我亦已不再能够就他手如三年前一样吃掉他喂过来的药。因为小诺正在回头看着我。
从他掌心拈起药,药刚送入口他已递过饮料。我接过瓶子,喝下一口送药。
药吃完他拿过瓶子旋好瓶盖仍是放在座位下,蹲下身望着我,“一会就好了。再忍一忍。嗯?”
我点头。点过头后垂下头。不看他。小诺正在回头看着我。我不能看他。我不能哭。
“眼镜摘下来吧。”他轻声道,“躺着还戴,不难受么?”
“我没事。快走吧。已经为我耽搁了太久。”我小声催促。不敢再与他这样相对。我怕再这样相对下去即使小诺正在回头看着我我也会忍不住流下眼泪。
“前面上高速后有服务站,要不要去一下?”他最后问我,在我摇头后他将我起身时滑落在我膝上的外套拉起搭好在我身上。轻轻关上车门。
安谙,或许照顾我已经成为你的一种习惯。我希望你能戒掉这习惯。我不值得你这样,不再配你这样。请你不要对我这样好。因为小诺就在你身畔。
车上高速,重新蜷躺在座椅中我抬眼看车窗外面飞速掠过的树顶尖。他开车还是这样既快且稳。跟三年前上半夜送旎旎去上海的宠物医院下半夜又为莫漠从上海赶回杭州一样既快且稳。
乐声流转,互相追逐。有时拢得很近近得让人觉得慰藉有时又远远错开如同尘世里我们一次次的挥手作别。就像这张碟子封面介绍所说,“图雷克这位纽约爱乐首席女指挥在八十四岁的晚年愈加平静和深邃,每个音符每个变奏都处理得异常清晰且端庄,敏感的指触纯正的风格感稳重而内敛宁静而致远。一如她曾说的‘我从不把这部作品当成炫人耳目的技巧表演。它是生命的体验。’”……车开这么快他让小诺系安全带了么?小诺会系安全带么?这是第几个变奏了?胃不那么难受了,眼睛也睁得累了,意识渐渐朦胧中我阖起眼帘在心里自问自答,好像是第十六个变奏吧,四十七小节的法国式序曲,是整个三十个变奏的分界,从下一个变奏开始明显比前面的变奏渐趋复杂,直到最后骤然回到平静朴素的主题,如同所有绚烂之极的终将归于平淡,所有曾经澎湃过的亦会转为寂寂幽然……
如果能够一直这样子在安谙的车里睡下去,一直这样子在安谙的身后睡下去,该有多好。意识将离的最后一刻,我忍不住这样奢想。
别人的戏演完了我还没退场
然而没有如果,如同我睡着一刻即使意识那样模糊也知道这不过都是我的奢想。
被安谙喊醒的时候,太阳眼镜斜斜歪在一边,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自己看上去一定很可笑很糗。急忙坐起身子扶好眼镜又顺手扑撸一下散在颊边的乱发。
“好些了么?”安谙问。站在车门外弯着身子垂头看我。
“好多了。”我仍是不看他,腿蜷太久坐起伸展开时才发现竟已酸麻。不想让他知道我竭力忍住把腿伸直落下,却还是给他看出了我脸上强自忍耐的挣扎。他弯身探进车里握手成拳一下一下在我腿上敲捶,我想说别敲别敲太难受了让我自己缓缓就好,可我不能说,说了就像是在撒娇。而我已不再能够跟他撒娇。
“下来走几步。”他敲了一会儿挽住我手臂把我搀扶下车。双脚着地的瞬间脚掌心如有万根针在扎。于这万根针在扎般的刺痛酸麻中我想起很久以前我们一起看的本山大叔的小品,他如何故意拿捏出本山大叔的铁岭腔说走几步走几步没事儿走几步。那时正是莫漠最萧索时分,我们除了动画片看的最多的就是本山大叔的小品。他学完我和莫漠哈哈大笑。他就笑望着我说旖旖你是东北人你来学不过我想你肯定没有我学得好学得像在语言方面我可是相当有天赋滴!
这么多过往这么多细节这么多过往里的细节再见到安谙后一点一滴我全部想起。
安谙你也想起来了对么,否则你为什么唇卷浅笑在我耳边轻声再道,“走几步走几步,没事儿,走几步。”南方人说不好儿话音,“没事儿”在你嘴里说起来谐趣稚拙。我想笑却怎样也笑不出,不由自主侧眸望你的瞬间你的眼里为什么又涌上浓浓忧伤。
“旖旖姐,你胃好些了么?”走了几步后小诺过来扶住我。
她扶住我的一刻我收起望着安谙的视线收起脸上对应着他的忧伤的忧伤亦从安谙手中抽出手臂,转头对小诺笑,“好多了。谢谢你,小诺。”
“旖旖姐你不要这样客气你是他的朋友就也是我的朋友朋友之间互相关心应该的。你千万不要这样客气!”小诺很惶急地道。这单纯的孩子竟连别人表示一点谢意都不好意思接受。
我微笑着望她,无法不喜欢她,她这样可爱不仅可爱还好看不仅好看还单纯我真为安谙感到高兴。是的高兴我是真心的为安谙感到高兴尽管我是这样一个虚伪的女人但说这话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矫饰你们必须得相信我。对她对安谙我除了祝福还是祝福。
“好,我不跟你客气。”我对小诺道。
腿脚刺麻已过。我在地上跺跺脚。脚跺在地上嘭嘭有声嘭嘭声中我仿佛又听到安谙几年前在“走几步”前跩一口铁岭腔说的,“你跺你也麻”。
记忆展呈到这种程度如何就不是妄念,而谁能告诉我我要如何去除这妄念……
远处有人齐声喊我名字我转头望去正是在殡葬馆统统不知去向的宋马陆三位师兄。他们此刻站在华夏公墓大门前俱对我绽露微笑,隔这么远我亦能看到他们笑容中的鼓励与支持。可是,没有用了呵三位亲爱的师兄。如今我所能做的就只是祝福。真诚的祝福。
松开小诺的手我说我自己可以了小诺我去拿一下我的包……
我尚未说完安谙接过话道包就放我车里吧回头我送你去机场。
我只好微笑说好。
我其实是想把包拿下来自己背着或放在三位师兄任何一位的车里。我一点不想安谙送我无论是机场还是去哪儿。我不想他送我。就像三年前他悄然走掉三年后我亦想悄然走掉不想面对离别的惨伤。
安谙,我想你是真的放下了吧,否则你不会要送我。
你眼中偶一浮现的忧伤只是你暂短的耽溺于回忆,对不对。
说完好后我不看安谙只对小诺道,“我去跟三位师兄一起走。这么久没见我想跟他们说说话。”
小诺关切道,“还是我扶你上山吧旖旖姐。”
我微笑,“我没事。好多了。”笑过回身向三位师兄慢慢走过去。身后的安谙你可在望着我。而不管你是不是在望着我,小诺就在你身边,你理应陪她走。我不过是偶然飘回的云彩,如果我的祝福果是真诚,我就不能遮覆住你和她的快乐与幸福。
华夏公墓的牌楼巍峨高耸,走到三位师兄身前我抬头仰望,这么高这牌楼这么高,是不是所有的公墓都要修筑这么高的牌楼,以证死亡的肃穆与端严。
陆师兄最是撑不住,见我走近急声道,“你干吗过来呀干吗不跟安谙一起走呀?”
我微笑,“我想你们了啊亲爱的师兄们。难道你们不想我吗?”
马师兄亦是有关切,“是因为那个女孩子吗?她是安谙现在的女朋友吗?”
宋师兄默默不说话,只是望着我,掩不住的好奇中带着些微寥落。
我继续笑,“是的吧。我没问。不过应该是的吧。”
陆师兄急得只差没嚷出来,“你怎么这么让人着急啊程旖旖你就不会试探一下问问吗?!”
马师兄也道,“是啊是啊你可以争取嘛只要他们没结婚就有希望啊即使结了婚也可以抢过来的呀!”
宋师兄这时从手包里翻出一包湿巾,走到我近前抽出一张轻轻拭抹我的脸。湿巾擦过脸上清清爽爽好不舒服我想我的脸上一定花花绿绿像只脏猫。一张拭抹不净宋师兄又抽出一张。我垂眼不看他,于他这兄长般的关怀体贴中感到直达心底的温暖。马陆两位师兄初时不说话,在宋师兄第二张湿巾试抹到一半时陆师兄突然蹿过来一把拽开宋师兄,恨恨道,“程旖旖没长手吗要你擦!擦就擦呗,擦吧擦吧就得了,安谙那孩子就在那边看着呢你还想他再误会吗?!”
我轻轻笑了笑,抬眼看着陆师兄,“没关系的陆师兄。他不会误会的。”我怎样都已与他无关了因为他已经有了小诺。又对宋师兄笑一笑,“谢谢你呵宋师兄我一定狼狈极了是不是?”
宋师兄不言,马师兄叹息,陆师兄转开眼睛看着别处道,“求你了程旖旖你饶了我们吧别再笑了!”
看着他们脸上真切的焦虑与着急,我就想多么好这世上还有这三位师兄永远力挺我。而不远处的安谙你在望着这边吗你对我亦有一点点关心吧,毕竟我们还是朋友呵。你甚至如我一样没有选择遗忘,我给你的记忆那么痛苦你也没有选择遗忘,我还有什么不满足。
人太过满足就容易懈怠,不再想那些不太现实的事情,以及再一次的追索和抗争。而我更是从来都没有追索抗争过。至此我似乎找到了答案那答案就是人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在爱情面前我从来都没有追索抗争过,我不知道怎样去追索去抗争,以前不知道,现在也还是不知道。人骨子里的东西真的是无法改变的。
懈怠中我感到身心俱疲身心俱疲的此刻我只想静静站在三位师兄边,静静地送完安师母。
安导的车这时也已经开到,我们不再说话默默看着安导从车上下来。他的儿子和儿媳跟他同车过来。他的儿子手里捧着安师母的骨灰盒。公墓阔大的停车场一时聚起跟过来的来宾。这些来宾在安导到来之前跟我们一样散在四处聊天。现在俱都沉默不言。
安导面上仍是看不出什么戚容。从我昨天第一眼看到他直到现在他一直都没有哭。安师母遗体告别时他没有哭。安师母遗体被推进焚尸炉时他也没有哭。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有多镇定自若,即使不认为他镇定自若也必佩服他斟破生死的洒脱。可是他不哭比哭更让我难过。因为我知道不哭下面定是隐藏着无法表述的痛伤。
一年半不见,一年半不见安导还是一年半前的老样子。头发没有再花白脸容也没有再衰败。他还是老样子。安师母猝死直到现在他还是老样子,看到学校领导会得微笑应对,看到友朋赶至也平静相招。我却仿佛看得见他不变脸容下溃疡一般慢慢侵蚀的创面,溃疡一般以他人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缓慢扩张。
安导,你哭一下好不好?哪怕只是掉几滴眼泪。你不要这样沉默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