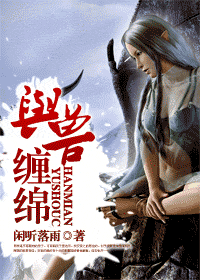或者缠绵,或者诀别-第10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一看穿行在这些古老建筑物间的旅人,看他们的脸上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喜欢这种行走的感觉,行走中有落寞。
遇到卖旧物旧首饰的小店子,我会进去转一转,店门推开的时候,门上挂的铃铛轻柔响起,我就仿佛回到某个过去时空,驼铃声声,微有恍惚。
那些旧物旧首饰,疏落地摆在玻璃橱柜或玻璃柜台里,时光在它们身上完全不起作用,它们只是在无尽岁月中等待,以不变的脸容等待新的主人。
遇到会说英文的店主,我们会聊一聊。那些店主总是很耐心很温和地告诉我,这条银镶红宝石的项链是十八世纪的,这只银酒杯是十六世纪的,这把佩剑是十七世纪某个子爵的。即使看出我不会买,也不妨碍他们的温和与耐心。或许因为大家都寂寞,有一个人说说话也好。
这样的古老城镇走得多了,我就觉得好像哪里都一样,都是被时光一笔一笔镌刻出来的,一笔一笔全是静默的沧桑。就有一点点了解莫漠当初,为什么她说她厌弃古老欧洲的奢华。因为哪里都一样,哪里都是一个人,哪里都寂寞,哪里都不会因为你的来去而改变,你亦不会因为哪里而改变。
永远是一个人。永远是一个人在行走中思念着一个人。
这样的古老城镇走得多了,我亦开始觉得厌弃。连行走都觉得厌弃。
我就开始怀念丽江,那只有素朴民宅而没有丝毫奢华装饰的小小四方的古城。可我知道,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回到那里。只能怀念。
而其实能够怀念也是好的。更多时候我连怀念都不敢。
此刻,我慢慢行走在这个叫枫泾的古镇,慢慢行走在安谙与小诺身后。
左手边是蜿蜒的河道。河道上有乌篷船缓缓划过。有的乌篷船上只有船夫。有的乌篷船上有三两游客。游客有的在说笑,有的在拍照。我就泛起久违的喜欢。这小小幽静的古镇,没有欧洲的奢华,只有丽江四方街的素朴,不会让人厌弃,只让人觉得亲近。
这小小幽静的古镇,像一本我看不懂的古书。安谙能看懂,安谙在前面带路,这里是程十发祖居,这里是吕吉人画馆,这里是朱学范生平陈列馆……我看不懂,就一路随着他的指点,闻着淡淡纸墨香,单纯地觉得好。
这小小幽静的古镇,是安谙的老家。
临河的院落,一家挨着一家,除开那些名人祖居和画馆,就是一些居居,有的人家对外开放,游客可以进去参观,门上贴着票价。有的人家门前支出摊子卖状元糕和天香豆腐干。小诺手里已经拎了两大袋,一袋是状元糕,蛋黄、椒盐、松子、香草、玫瑰、桂花她一样挑了一块。另一袋是天香豆腐干。她边走边吃,不时喂安谙吃一口。又回头问我吃不吃,我笑着摇摇头。
临河的院落,一家挨着一家,每一家都有青黑色的木门,青黑色的木门前是幽窄狭长的石板路。石板路向下有石阶,直探入蜿蜒的小河。跟石板路一样,石阶的边缘与石面俱在过往岁月被无数双脚踩磨得温润涓光。走在上面,我就开始恍惚,看着脚下的石阶与石板路,仿佛回到了丽江的四方街。千帆阅尽,百转沧桑,偶一回眸时候,没想到我还会看到这相似的石阶与石板路。而这相似的石阶与石板路上,它们温润涓光的石面,可会映着我脸上隐忍的忧伤。
恍惚中,我看到安谙拿出钥匙在开一扇青黑色木门。他的钥匙包里拴着好多把钥匙,不知这好多把钥匙里可有杭州安导闲置房子的钥匙。
青黑色木门“吱钮”一声被缓慢推开。木门推开的瞬间,眼前清幽的天井,天井中葳蕤葱茂的巨大盆栽,还有天井一角种着的一尾芭蕉几丛修竹,绿色枝叶雨水洗过后青艳明亮,让我恍惚愈甚。我知道这不是丽江,我知道这不过是安谙安排给我的下一个场景,我知道过去的一切都已过去,但是眼前所见,陌生却亲切,情如旧欢。
身旁小诺连连惊叫,“呀,你家老宅这么好呀!这一座宅子现在要值好多钱呢!”
安谙淡笑一下,“你呀,怎么就认识孔方兄。”
小诺笑,“本来嘛。你不要一听钱就觉得俗。一件东西是否珍贵最后还不是要用钱来衡量?否则干吗要用‘价值连城’形容那些国宝!”蹦蹦跳跳地绕天井跑了一圈,摸摸盆栽,又拽了拽芭蕉叶子,芭蕉叶子上的雨水滚落,滴在她脖颈里,带起她咯咯一阵轻笑。“或者留着给你作故居,你这样一个大作家,哦?”小诺嬉笑着调侃安谙。
安谙笑意愈深,“没死就搞所谓名人故居,这么恶心的事情还是留着让余秋雨一个人做吧。我可做不来。”笑过转头看着我,“去洗个澡吧。洗完澡换身衣服。”放下手里的菜蔬,拿过我肩上的包,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牵起我的手,向南首一处房间走去。
他的手一如三年前宽厚温暖,初时只是轻握,片刻即一紧再紧。我冰冷的指尖感受到他掌心的温暖,缓慢融化,缓慢浸达我的四肢百骸。
三年前他每一次握住我手我都会心跳加快,可是现在,没有心跳加快,我只是觉得温暖,入骨入心的温暖。这温暖令我如此疲惫,如此软弱,如此想流泪。这个叫枫泾的古镇亦令我如此疲惫,如此软弱,如此想流泪。这座安家的老宅,亦然。
看不到身后小诺可有看着我们,不知道她看到安谙牵我的手脸上又会作何表情,我如此贪恋这片刻的温暖,贪恋到不够力气和勇气挣出我的手。我只是默默感受这温暖,用力记住这温暖,用手用心用力记住这温暖。原谅我从来都是一个自私的女人,我知道接下来总有一个时刻会放手,不是我也会是他,我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暂短停留,可是现在,请允许我贪恋,即使小诺就在身后看着他和我。
他牵着我走到南首房间的房门前,即放开了我的手。他手放开的一刻,我心里一阵微悸,带着冰棱的冷气。我不由自主转头看他,他没有看我,只是在钥匙包里挑钥匙,挑了一把,插进锁孔,扭一扭,不是,再挑一把钥匙,再插进锁孔,这次是了。
房门打开。我看着房间地面铺着的天青色地砖,问他用换鞋吗。他说不用。走进房间将我的包放在一张很大的书桌上。书桌一如杭州他房间里的书桌,整整齐齐码着一摞书。他回头看着我轻声道,“进来吧。这是我的房间。今晚你住这吧。”
我走进房间,被他握过又松开的手贴着腿侧悄握成拳,手背已复寒凉,或许握成拳后掌心能留得多一刻他掌心的温暖。
环视这间屋子,跟云南我们逗留参观过的古老民居不同,举架很高,面积很大,老式木窗子高窄狭长,采光却不是很好,或许是因为阴天。看不出太多装修的痕迹,除了地上铺着天青色地砖。墙壁可能粉刷过,但已满是斑斑水渍,像一张敷粉亦掩不住老年斑的脸。没有什么零碎摆设,一桌,一椅,三面墙满塞着书的书柜顶天立地,一只不大的单门衣柜挤在门与墙壁的夹角,临窗放着单人床,床上被褥干净洁白。
他说过他喜欢白色的被褥,即使洗起来比较麻烦。他说睡在白色的被褥里,让他即使沉于睡眠也能保有一丝醒觉,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睡前在做什么,醒后又该做什么。
重逢后,这是我们第一次独处于这样的封闭空间。我微有紧张,微有惊惶。进房后站在门边,不知道该再进一步,还是站在原地。不知道该关上门,还是让门开着。
他拉开书桌前的椅子,对我道,“坐吧。”我走过去坐下。
他关门。关完门走到床前,探手进被摸了摸,从床褥下抽出一只连线插头插进床头墙壁的电源插座里。我知道,那一定是电热毯。江南阴湿天气里被褥会反湿,电热毯可烘掉被褥里的一些湿气。
电热毯插好,他又抖了抖被子,将被子抖得蓬松些,这样子电热毯的热度就会发散得均匀些。
我看着他做这一切。看着他再自然没有地做这一切。看着他抖好被子从我身前走过,推开卫生间的门进去。壁灯撚亮。片刻后有水声轻缓响起,细细弱弱落在地面,如谁隐忍的呜咽。
“天阴,热水器里的水不是很热。”水声止歇他从卫生间出来对我说,“不要动冷水阀。我都调好了。”
我点点头。没有感动。只是想哭。为他这一如既往的细心与体贴。为他三年后仍记得我总调不好洗澡水,总不记得阴天时候提前插上电热毯。
眼睛看着地砖,地砖上有浅浅错落脚印,是我们带进来的。“好。”片刻后我轻声说。
“卫生间里有拖鞋。是我的。鞋大。小心点。别摔倒了。”
“好。”
他稍有沉默,“洗发水带了么?”
我想了想,“好像没带。”
“用我的吧。”
“好。”
“沐浴液洁面乳呢?”他再问。
“……也没带。”早上出门前,我是用清水洗的脸。想过用他遗落的BIODROGA,却到底不敢触碰。
“也用我的吧。”却在我再一个“好”将要出口时,他轻声续道,“反正只今天一晚和明天一早。”
我僵住,不知道该抬起头还是继续垂着头,不知道怎样将唇齿间将出未出的这个“好”咽下去。眼眶里有泪水在转。我想我的戏份要演完了。
再次沉默。再次沉默后,他轻声道,“去洗吧。暖一暖。你的手还是那么冰……”
我想起三年前端午那日我们一起去嘉兴火车上半真半假玩笑地临场做戏,那时面对他愈靠愈近的脸庞我不知如何应答,慌乱中我说我忘词儿了,下句该说什么来着。他转身笑笑说没有下句给你背了,你老忘词。
现在,对不起导演我又忘词儿了。我不知道下句该说什么。三年前我可以玩笑着说手凉没人疼。三年后的现在,我只有沉默着不知所措。
他慢慢靠近我,抬手轻拢起我耳旁湿发,望着我耳廓上满满一排细小耳钉,他指尖一只一只耳钉抚过,轻声问,“打这么多耳洞,疼不疼?”
为什么牙齿依旧咬得这么用力甚至更用力我却再也止不住眼泪。当第一滴泪水终于挣出时候,仿佛听得到身体松泄下来的声音,那声音如同一抹叹息,叹息中我任泪水汹涌而下。
当着小诺的面我不能哭。当着三位师兄的面我不能哭。当着安谙的面我也不想哭。即使饭店里看到他喝完酒吐过后苍白的脸,当着那么多的人面我也能死忍住。可是现在,我却再也忍不住。为他这一句疼不疼。为这一句原本我该问他的,疼不疼。
安谙,你疼不疼。三年里,你是不是比我还疼。
安谙,我没脸说疼。我的疼,不过是我自找的惩罚。
那部法国电影的最后,断腿的工程师挽着眼肓的音乐家向教堂走去,侍应生站在他们身后望着他们,却在将进教堂时候,工程师松开眼肓的音乐家,转身一拐一跳以他所能用最快的速度踉跄着走近侍应生,紧紧抱住了他。最后的拥抱时分,他吻了吻侍应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我读懂了他眼中的心疼与怜惜。原来,他是知道的。他什么都知道,他只是无法给他爱与承诺。
安谙,你也知道的,是不是。你也无法再给我爱与承诺了,是不是。
他蹲下来,蹲在我身前,抬手用指腹轻轻拭掉我的泪。旧的眼泪没流尽新的眼泪涌出来。他的指腹不再拭抹我的泪,泪那么汹涌怎么拭得完,他只是抚着我脸颊,自眉至唇,最后留在我唇角的笑窝。那笑窝不再闪烁,那笑窝现在凝着眼泪。
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