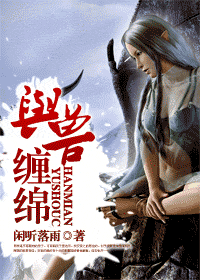或者缠绵,或者诀别-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微笑,年底转正。
那就难怪这么喜欢高大全了。
高大全又是谁我不认识啊。
他一声长叹,God!让我如何对你说?
失掉他我就失掉整个阳光
我想大多数人一生中总会或多或少有几个朋友。不是出于利益,抛开各自的学历地位家庭背景社会角色,没有任何目的和企图,完全用心交流。只讲感觉。也许一年几年见不上一面,平时各自为生活打拚,久不联系,看似疏远,却都活在彼此的心坎里。
或许只是寂寞时一个午夜电话,一封寥寥数语的E…mail,一张贺年卡,一件挂号邮递的小礼物,就能打开久已关闭的启动程序,就能抚慰对方日益坚冷憔悴的心。友情再度升华。绽放钻石般光华。这样的朋友,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只能碰到一个。一个,就已足矣。
早上没来得及吃饭,一睁眼就八点了,拽件衣服胡乱套上,头发都没梳。
都怪那臭小孩,昨晚把那个什么《本能》关掉后,我说今天就到这吧已经很晚了。他却执意换了一部《勇敢的心》。说是奥斯卡获奖影片,男主人公高大魁梧英雄盖世宁死不屈正适合我的欣赏水准。那么长的一部片子,看完都快一点了。又那么好看。对极我胃口。躺下后还兀自兴奋久久不能平静。
荡气回肠的主题音乐。我要记住,弹出来。
柔情似水的苏菲·玛索,目光幽怨,足以淹死天下男人。
我问安谙华莱士到底爱谁。
两个都爱。
那叫什么爱?
那为什么不叫爱!
爱是唯一是专一。
爱分很多种就像你喜欢吃笋也喜欢吃速食面。
那她们两个哪个是笋哪个是速食面?
你问华莱士或者你自己觉得哪个该是哪个。他把头靠在我肩上。
我用食指把他脑袋顶开,哎哎哎你干嘛呀?
靠一下嘛不要这么小气嘛。
怪热的。
那开空调。竟真的把空调打开了。
算了算了给你靠一下吧把空调关掉怪费的。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他胜利地笑,喂,你还真能省耶。
耶什么耶拜托你说话不要这么嗲好不好跟我们学校中文系的小女生似的。我故作嫌恶的斥他。
他吐吐舌头,关掉空调,脑袋实实靠在我肩上,头顶心抵着我下巴,不再说话。
华莱士被推上刑台。苏菲·玛索瘫坐在临街森严的皇宫里伤心欲绝。她有了他的孩子。那孩子是一个遗腹子。永远不可能知道父亲的样子甚至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自由!华莱士最后高喊。他最后看见的是他的妻子。他最爱的还是他妻子。苏菲·玛索可以是笋也可以是速食面。他妻子却是圣诞大餐火鸡牛扒。苏菲·玛索的泪水滚落下来。腹中的小生命蠢蠢而动。他是她的最爱。
影片结束。我泪流满面。安谙伸完懒腰蹲在我面前,你还挺投入。他说。把纸巾盒塞在我手里。我抽出一张吸鼻子擤鼻涕。他拨开我脸旁的头发眼睛发亮看着我。怎么样好看吧?还行,跟《焦裕禄》《周恩来》差不多好。姐姐你能不能换一个参照物?他向后跌倒,坐在地上。我一共也没看过几部电影嘛。那以后听话多看点。才不要这是最后一次又浪费时间又浪费感情我可没有这么闲。我站起来,看一眼表,天哪这么晚了吗明天起不来怎么办!?那就不去上学了跟我在家看DVD。他蹦起来提议。还看!我瞪他一眼,都是你害的。他探手过来在我脸上轻轻摸一下。我急忙侧头避开。他竖一根手指到我眼前,纸巾屑。他心无城府的笑。
正吃泡面,电话铃响,陆师兄捞起话筒随即递给我。我以为是安谙,昨晚临睡前他说过让我中午回去吃他做的饭。喜滋滋接过话筒,听到的却是一个疲惫沙哑的女人声音。毫无铺垫劈头就是一句能出来吗我想见你立刻。愣了足有五秒,我才反应过来,是莫漠。我看一眼陆师兄说,行,在哪?她说你出来吧我就在浙大门口。
看到莫漠我几乎不敢认。她跟半年前完全判若两人。原本飘逸轻扬的长发挽在脑后梳成一只圆圆的太太髻。手绣旗袍。铂金镶钻饰品一样不落。高贵,雍容。神情萧索。而从前的她,T恤牛仔就是最爱。轻舞飞扬像早春的薄雪。
我结婚了。她一句话把我击倒当地。
因为我知道,她不可能嫁了给她所爱的人。
因为我还知道,她这辈子再不可能爱上第二个男人。
因为我又知道,像她这样的女子,所嫁非爱,注定会是一场悲剧。
他?我还是垂死挣扎地问了一句,明知是徒劳,明知她听到会痛,也还是忍不住。
眼泪不出所料刷一下流了她满脸。路人开始对我们频频回望。
我慌慌地说,去我那儿吧。
是他爸爸。这是莫漠见我后说的第二句话。我险些叫厨房的安谙进来给我人工急救。
你说什么?我一下子跳起来,恨不得自己双耳失聪。
是他爸爸。她慢慢重复一遍。神情木然。他爸跟他妈离婚后他爸一直未婚。春节的时候我认识了他爸。上礼拜二注的册。
你疯了?怎么可以这样!太离谱了!我不顾一切大叫。
安谙冲进来问怎么了。
我狠狠凶凶地说,这没你事儿!随即泪落如雨。
莫漠。我最好的朋友。硕果仅存的朋友。相交四年的朋友。陪着她苦看着她痛了四年的朋友。从头到尾对她说不要放弃却比她还要彻底绝望了四年的朋友。我友情的全部支柱。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她的痴情不会有任何结果,却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收尾。她太狠了。爱一个男人爱到不能呼吸,背水一战,孤注一掷,全然豁出去了。
我抓住她冰冷的手,泣不成声,是我害了你。是我不好。是我不该对你说不要放弃。
她轻轻抚摸我无力披垂的长发,软软地说,我是真心想嫁的。他……他爸爸对我很好。我很幸福。
我把脸埋在她手心里,拼命摇头,却发不出声音。
她的声音遥远地送进我耳鼓,我真的很幸福呵。至少,我可以以家人的身份常常、时时地听到他的消息,在分机里听到他跟他爸爸通电话的声音,没有人时悄悄翻看他小时候的日记,名正言顺地注视书橱里他的相片,替他爸爸给他发Email……
我堵住她的嘴,不让她再说下去,感同身受的心痛到滴血。
她温柔握住按在她嘴巴上的我的手,柔声说,我不能没有他,即使做他后妈,我也不能没有他。我的世界不能没有他。
谢谢你,四年来一直对我说不要放弃。这是我一生中接受的最好的建议和鼓励。
爱他本身并不痛苦。第一次见他,第一眼看他,我就知道他是我这辈子的阳光,是我的清凉泉水,是我的在劫难逃。爱他,悲伤欲绝,也欣喜莫名。失掉他,我就失掉整个阳光。
一千多个寂寞夜晚,我默念着他的名字入睡。每次去他现在生活着的那座城市,穿过陌生的街道,我都会想他是不是也这样横穿过我正走着的马路。无数个万家灯火,我会想他曾在哪一盏灯下流连。我会为一个像他的背影惊悸,追逐到下一个街角。然后泪湿双襟地呆立,为那个背影的消逝哭泣。他无心牵过的我的手,我常执起凝视。他让我充满无法言喻的柔情,也为我带来无可解脱的绝望。你知不知道黄昏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断送一生憔悴。
爱他并不痛苦。也许时间太久已经麻木。真正的痛苦是他依然存在。想到我和他共同生活在世间我就如坐针毡。他有他独立的心,独立的呼吸,独立的行动。他会有他真正爱惟一爱的女人做他的妻。而他跟我不再有任何关系。他跟我从此隔绝在世间,各自生活两个绝缘的圈子,我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他的进步,他的悲喜,他的焦虑,他的成绩。我再也捕捉不到感受不到他的存在他的气息,我只能绝望地告诉自己他也还活着,和我一样还活着。比我幸福的活着。跟我毫不相干的活着。我就痛苦得恨不得死掉。与其如此,既然我又没有勇气真正去死,那,就退一步,海阔天空。
莫漠,是我错了。
我不该让你坚持。
我应该让你放弃。
我以为从没有什么可以对抗时间。
我以为再没有想念可以长得过时间。
我以为也许放弃,才能拥有,不再见面,他才会偶尔把你记起……
我以为在回忆中寂寞的香气里,开到荼蘼的花朵终会再次翩然起舞。
我以为我们大家都会渐渐好起来,各自的幸福和陷落,有如此刻的沉沉落日,正在销歇的紫金光影,流离失散。
我以为,
我以为,
我以为没有人可以做到一生只爱一个人,在这个不再坚守信仰飘零的年代。
我以为走过去你会找到属于你的天。
现在我知道是我错了。
莫漠,是我错了。
猝不及防的吻
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我会非常非常脆弱。脆弱到渴望一个胸膛让我埋头哭泣。这个胸膛从来不曾出现。我也就从来不曾埋在里面哭泣。
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我会非常非常孤寂。孤寂得想找一个人放纵。这个人选曾经有过一个,现在她做了她爱的男人的后妈,夜夜无眠躺在她爱的男人的爸爸的身畔,自然也就不能陪我放纵。
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我会非常非常自弃。我会把一整瓶红酒喝掉,然后对着自己的影子抽泣。
在生命的这个时刻,我不知道我到底想怎么样。莫漠绝望冷静的脸在眼前交相叠映。是我害了她。如果我不告诉她一直坚持如果我没有给她鼓励加劲她也许不会陷得这么深这么彻底。。电子书是我害了她。她才二十五岁。我心疼她年轻的生命,从此陪伴在一个年近半百的男人身旁,慢慢枯萎。最重要的是,那不是她的所爱。是我害了她。她一向柔弱顺从善良固执天真的相信我灌输给她的信念以为只要坚持就会有结果。是我害了我。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狗头军师。
她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朋友啊。
除了她,我还有谁?
身旁是一个沉默注视我的男人,而我在喝第二瓶红酒的最后一杯。
有液体一滴一滴跌入酒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的眼泪。胸口那块叫心脏的地方隐隐抽痛。我想我也许应该再来一杯。
身旁的男人伸手夺过我的酒杯,用一块湿软的毛巾给我擦脸。我一个劲看着他傻笑,说一些不明所以的傻话。擦完的脸又是瞬间淌满眼泪,我倒在那个男人怀中大声哭泣。
隐隐约约他问我为什么。我语无伦次反问他情为何物。他好像说就是我和你。我把头抵在他胸前说我不认识你。他的手穿过我的乌黑长发,轻轻抱我在怀。
就是这样吧。父亲的或者是男人的怀抱。我都不曾有过。父亲的或者是男人的怀抱。就是这样吧。
我埋脸在他温暖的胸膛,任泪流成海。
他让我有险象环生的安全感,未曾有过的依赖感。他注视我的目光干净明朗,抱着我的手单纯坦荡。
他不会让我想起多年前那丑陋恶心的一幕。
即使他接下去会做他一直想做的,要他一直想要的,即使坚守了这么多年的东西,今朝就会失去,我也不会抗拒。
我醉了。
我不介意。
随他拿去。
是不是所有的宿醉过后,都是混沌一片,懵然无知。
迷乱朦胧中似曾有过的温存,渺然如梦,难以搜索。
我看着身旁二米远宽大沙发上酣睡着的男人,鹅黄色毛毯,安然的睡脸。彼此齐整的衣服。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什么都没有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