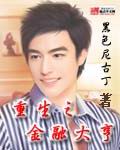鱼在金融海啸中-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米尔森先生,您给我看的是INSEAD商学院的入学申请书?”
他点头,“不知苏小姐是否听说过INSEAD?”
开玩笑吗?欧洲排名第一的INSEAD商学院,校址就在举世闻名的法国枫丹白露,金融专业的梦想之车。她有一个学姐曾经为了能够进入INSEAD而放弃了自己的六位数年薪,学成之后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成为麦肯锡亚太区的唯一女性合伙人,短短数年,脱胎换骨,这样大名鼎鼎的商学院,她怎么可能没听说过?
单是这样还不够让她对这个词如此震惊,事实上,她身边还有一个曾在那里生活过的男人,INSEAD是陈苏雷的母校。他心情好的时候会听法国香颂,偶尔在她耳边提起枫丹白露的白桦林,还有那首模糊的法语歌,温柔低缓,像一张看不到边际的网,将她层层缠绕,再也不能挣扎。
不能再想下去了,苏小鱼在桌底下左手掐右手地阻止自己的神思涣散,这里是仲银集团的会议室,面前坐的是米尔森·帕克,绝不是她应该恍惚出神的时候。
“我知道INSEAD商学院。”她开口,给予肯定答复。
米尔森微笑继续,“苏小姐,INSEAD与国内商学院有一些交流合作项目,我作为他们的特聘顾问参与本次面试。亚太区INSEAD今年有一个中国优秀学生全额奖学金招纳的名额,有人向我推荐了你。我看了他给我的推荐材料,也查了一个你的笔试成绩,两者都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有人向米尔森推荐自己?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苏小鱼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问他那个人究竟是谁,但一转念就觉得在这个当口谈这个问题很是不妥,嘴已经张开了,她最后只说了一声“谢谢”。
“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这个推荐并不太看好。恕我直言,你年纪尚轻,虽然在BLM工作过,后来又参与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收购与重组项目,但实际工作时间并不长,更没有什么管理层的经验,与INSEAD学院的要求还有些距离。”
“我知道,一般商学院都倾向于培养一些有高层管理经验的学员,这方面的经验我的确很欠缺。”还在消化刚才的消息,苏小鱼闻言并没有辩解,实话实说。
米尔森一直带着笑的眼里流露出一点儿赞赏的目光,再次开口:“名额只有一个,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也在数个候选人之间权衡了许久,直到昨天下午有幸与你面对面聊过之后,我才真正确定,之前的那些问题应该都不足以掩盖你的优点。”
“昨天……”那是她的惨痛回忆,苏小鱼至今耿耿于怀。
他眨眼,“就是昨天,你说‘没有关系的确很麻烦,但是真的想做成一件事的话,总有办法’。还说‘做生意嘛,目标一定要准,但中间的路怎么走都在我们自己,一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关系也一样,没有关系就创造关系。’是不是?”
他慢慢地复述她的无心之语,居然一字不漏,说完还伸手轻轻拍了两下,夸了句“很精彩”。
那句话不是她说的……苏小鱼心里一窘,但米尔森继续说了下去:“所谓经验,都是需要时日积累的,但坚持与变通这两者之间的微妙权衡却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鉴于你在各方面的出色表现,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将这个名额留给你。”
他说完之后微笑地看着她,但她却只是沉默,那份摊开的文件夹就在眼前,雪白纸上满页的黑色字符仿佛要飘散开来。苏小鱼心里纷乱杂陈,INSEAD学院是国际一流的商学院,别人求也求不得的锦绣前程。其实是该觉得狂喜的,但这一切来得突然,她竟觉得惶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自己又该如何应对。
“苏小姐?”看她一径沉默,米尔森又开口。
她回神,抬眼看着他,“米尔森先生,这些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需要想一想。”
他微笑,“当然,苏小姐,如果你还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的助理詹妮小姐,她会为你留言。”
知道这是委婉提醒她时间已到,苏小鱼点头站起来,道谢之后才转身往外走,手已经落在门把手上,又克制不住地转过身来。
米尔森仍坐在原来的位子上,见她回头,只挑了挑眉。
“米尔森先生……”她迟疑,“我能不能知道,是谁推荐了我?”
米尔森听完但笑不语,但苏小鱼坚持地看着他,他最后终于开口:“不好意思苏小姐,恕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不过我想你心里一定是有答案的,是不是?”
心里一定是有答案的……
是,她知道是谁给过她推荐,至今还对汤仲文的出手相助心存感激,但现在情况已经脱离了她所能理解的范畴,难道汤仲文真的如此看好她?除了那封致国内商学院的推荐信之外,又在她所不知道的时候向米尔森作出了另一份推荐?
为什么?
她自问她并不是什么天降英才,读书全靠刻苦,刚进大学的时候英语口语跟不上其他人,整天就发戴着耳机听国际台,睡觉时的梦话都是叽哩咕噜的。后来进了BLM,身边全是顶尖的人才,拿出来的履历金光闪闪,唯独她出身普通,没有任何背景的员工凭什么能够留在公司?能凭的不过是咬牙苦练。
说句实在话,苏小鱼从未相信过天上掉馅饼这等好中,她这辈子唯一称得上匪夷所思的幸运事就是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遇到了陈苏雷。即便如此,她也不认为那是一劳永逸,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清楚他是只谈过程不谈结果的男人,所以从未想过今后能够依靠他过上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更好的生活谁不想,但她心里明白,如果她可以,不用他的她也能得到,如果她不可以,用他的也不长久,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从未放弃过让自己更高一些、更强一些的努力,就算明知苏雷快,她也一意孤行地想要考MBA。但现在发生的一切她无法理解,那是INSEAD商学院在中国区唯一的全额奖学金名字,不知有多少人梦寐以求,汤仲文竟然推荐她这样普普通通的一个苏小鱼,为什么!她又凭什么?
或者不是他?但不是他,又会是谁?
她眼里全是复杂,米尔森倒甚是耐心,也不催她,安静地等。后来想起什么,又补了一句:“INAEAD的亚洲校区就在新加坡,与国内往来很宿命,你不必太担心。”
她仍是满心混乱,只听到“新加坡”三个字就慢慢地垂下头来,对米尔森笑了一下,接着再次混乱,推门走了出去。
会客区里已经看不到杨在心,不知她去了哪里,此时此刻的苏小鱼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想,詹妮小姐很客气地把她送到电梯处,道别时一脸微笑。
电梯里没有人,下降时安静无声。终于只有她一个了,苏小鱼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来,手指一动就想打出去。
熟悉的号码设定的是单键拨号,她突然害怕起来,又一指按断了这个电话。
拨给他,然后说什么?说我得到了INSEAD商学院的入学资格?还是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前任Boss汤仲文的推荐?
汤仲文……
这三个字让她太阳穴突地一跳。是了,她现在该找的人并不是苏雷,是汤仲文。
她不想自作多情,但汤仲文之前的种种表现太过异常,再加上这个推荐,她要是再假装一切都是空气,那就太假了。
想到这里,苏小鱼再次低头按键,电话接通时电梯门正好向两边滑开,汤仲文的声音清晰地落入她耳中,仍是连名带姓的三个字:“苏小鱼。”
很巧,此时的汤仲文刚刚结束在嘉里中心的一次会谈,这个电话拨进来时他已经走在地下车库里。低头看到号码,他突然地停下脚步,走在他身后的范闻正与助理讲话,也没提防,差点儿撞上他,接着便听到他说出的那三个字。
习惯了自家兄弟因苏小鱼而偶尔发作的异常状态,范闻苦笑着摇头,拉着助理继续往前走。
苏小鱼在电话里说得很简单,就问了一句:“文森,你有空吗?我想和你见面。”
他说“好”,只是自己在嘉里中心附近,回到浦东还有一段时间。说完才想叹息,又在心里对自己一讪。
她却没觉得他异样,立刻答了他:“那正好,我也在附近,现在这过来,等会儿见。”
第十八章 苏小鱼的穷人的自尊
穷人的自尊就是,明知要不起,却说是我不想要。
——苏小鱼
1
久光后街,任何时间都是人潮熙攘,车流密集,等待进入shopping mall地下车库的各色车辆沿街排成长龙,挪动速度缓慢。街边是整排的各国餐厅,下着些微寒雨的午后,临窗一层白蒙蒙的雾气,里外两个世界都是模糊的。
苏小鱼到达coffee bean的时候汤仲文已经在了,独自靠窗坐着。就这么一点儿时间,他居然仍在工作,低头看着掌上电脑,沉默的侧脸,衬着窗上的那一层模糊白雾,更显得五官深刻。
她在来时的地铁上想好了许多问题,走过去的时候脚 下却开始迟疑退缩,突然不想再往前走,很想转身离开这个地方,离开汤仲文的视线范围。
来不及了,他已经看到她了,在对她点头。
两个人面对面之后的第一名话是汤仲文说的:“要喝什么?”
她刚才心神恍惚,居然忘记叫东西喝,想站起来去柜台,他却先她一步,立起身低身看她,又问了一句:“要喝什么?”
她被动地仰头看他,来不及说话他便替她决定了,“巧克力吧,等一下。”
他说完便转身,苏小鱼唯一能做的就是望着他的背景发呆。汤仲文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给其他人带来很大的压力,收银台的小姐与他说话时有些紧张,最后还找错了钱,隔着那么远的距离,苏小鱼都能看到她耳根都红了。
她也一样,一直是有点儿怕他的,她至今都能够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对她说出deadline这个词时的压迫感,那种感觉太强烈了,以至于以后她与他所有的交流中,都不自觉地小心翼翼。
他在她心目中一直是那个有着完美主义强迫症的工作狂,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确定的。那么他呢?一直以来,究竟是怎样想她的?
没时间想太多,汤仲文已经走回她面前,坐下时把手中那个银色的号码牌放到桌上,就在他咖啡杯的旁边。
那杯咖啡是满的,杯沿雪白,一丝线喝过的痕迹都没有,苏小鱼开口的时候眼光落在上面,好像那是一件多么值得一看的美物。
她的第一句话是:“文森,谢谢你的推荐。”
隔了数秒才听到他的回答,只几个字:“不用谢我!”然后终于伸出手,端起了那个咖啡杯。
眼前的目标凭空失去,苏小鱼的目光却没有随着那个咖啡杯上移,仍留在空荡荡的原地。她沉默了。
他也不说话,等她。
这个coffee bean里永远都很满,身边充满了谈笑私语,一片嘈杂,唯独他们两个安静如斯。小姐走过来送上巧克力的时候着实迟疑了一下,放下之后收起那个银色号牌,倒退着走了,一句话都没敢多说。
透明玻璃杯里的热巧克力,颜色很淡,苏小鱼伸手去捧,隔着厚厚的玻璃,热度一点儿一点儿地传到掌心里,低头喝了一口,果然是淡的,与她习惯的浓郁味道天差地别。
她原是有无数的话想说,只这一口便被冲得淡而无味,心里混乱,没想到他应得那样快。自那个可怕的雨夜之后,她也模糊的感觉到他对她的一些不同,但每次想到最后都觉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