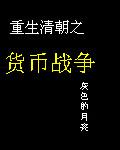鸦片战争实录-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这篇文章很费解。大体的意思是这样:在这个曰益走下坡路的衰世,而人们却鼾声大作,沉沉入睡。但“山中之民”在天地与神人的支持下,即将大声地呐喊着,蜂拥而未了。
有的评论家认为,龚自珍以这篇文章预告了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等的农民革命战争。这种说法也许太过分了一些,但是尽管龚白珍本人并不意识,他确实为下一个时代投射了光芒。
龚白珍在镇江庙会的人群中,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不久前接触过的各种人的面影。他想起厂曾任两广总督、当代首屈一指的学者、 白发皓首的阮元。阮元已经功成名遂,当时正隐居在扬州,他曾和来访的龚自珍淡沦了许多经学上的问题。
第6节:逃出首都的诗人(3)
正如《己亥杂诗》中所说的那样:“谈经却忘三公贵。”龚自珍曾和阮元畅谈得入了迷,甚至忘记了对方是被人誉为国家柱石的高贵的大人物。
龚自珍不由得不想起另一个给人的感觉跟阮元完全相反的人。
这个人就是林则徐。他已担任钦差大臣,应当已到达任地广州,在从事政务活动了。朝廷派他去广州是为了禁绝鸦片走私进口的。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再也不能放置不管了。
“林公是准备去死吗?”诗人的脑子卫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这是不是由于于旅途的劳累, 从脑子里偶然冒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呢?
“不!不是胡思乱想!”他在内心里跟自己这么说。
他这么想是有根据的。林则徐拼出一死去广州,这本身就是根据。
一想起林则徐。诗人的脑子里就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宦南诗社同人们的面影。
“多么珍贵的朋友啊!”龚白珍想到这里,产生一种陶醉的感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的眼睛里再一次涌出了泪水。
第7节:宣南诗社(1)
宣南诗社
中国的读书人一定要写诗,这可能是一种涵养锻炼,在调整平仄和音韵以及思考对句的过程中,以求得精神的平衡。写诗在中国的读书人中间十分普及,日本写短歌或俳句的人很多,这两者十分相似。
日本作俳句或短歌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称得上俳人或歌人的人并不多。同样,中国所谓的诗人,是指那些能写出极其优秀诗篇的人。中国并无诗人这种职业,诗人大多是官吏,如杜甫,李白、白居易,都是官吏。陶渊明辞官之后,并不是靠写诗乞饭,而是回到田园,耕田种地,以此来维持生汁。
诗是感情的抒发,是对人及自然的观察,其根本是一种表现的欲望,希望有人来读它,褒奖或批评它。它是解除人的孤独感的一种手段。所以人们喜欢同气味相投的人一起进行写诗活动,因此就产生了“集团”。
龚白珍所属的集团称作“宣南诗社”,同人中不少人都具有浓厚的公羊学的倾向。
所谓“公羊”,是孔子所编《春秋》的注释书之一。这种对《经》所作的解释,称之为“传”。《春秋》有公羊、左氏、谷梁三传。就详细注释历史的事实来说,《左氏传》最为杰出;《公羊传》则把重点放在贯穿于史实之中的理念上。《公羊传》尊重所谓的“微言大义”,是基于这样的解释:孔子在《春秋》这样枯燥无味的史实罗列中施加了深刻的用意,批判了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区别“华夷”——即文明和野蛮——的观念是极其强烈的。拿《春秋》来说,在谈到文明的国家时,如称齐人、秦人,都要加一个“人”字,而在谈到野蛮的国家时,仅以夷、狄、戎等来表示,不加“人”字。不过,经常有例外。如僖公三十三年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殼。”这就是例外。
人们对这个例外作这样的解释:给中华之国晋加人,对夷狄的姜戎不加人,这是遵照一般的惯例。但对中华的一国秦也不加人,这是因为秦在这次战争中搅乱了人道,因此不给它加人,意思是把它视同夷狄。相反,野蛮的国家因有善行,有时也称作狄人。
在记述无关紧要的事实的文章中插进激烈的历史批判,正是公羊学所重视的。随着历史批判精神的增强,这种学风必然带上政治的色采。不仅是对历史,对现实的政治也投以批判的眼光。所以学习公羊学的人,一般都是从历史批判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和批判,在行政组织、国防、经济、漕运、产业等各个领域中,对实际政治表示深刻的关心,并不断地加以评沦。
中国在宋代完成的朱子学被视为正统的学问。朱子学的重点是放在文献批判上,终于产生了象南末王应麟那样的考证学者。清朝因袭明朝的制度,也把朱子学当作官学。
清代的学问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证”,清代学术的精华就是考证学。考证需要严格的批判精神和合理主义,因此可以称之为近代的科学的学问。但是。其末流还是堕落到为考证而考证。拼命地进行考证,但这究竟有什么用呢?——在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因此,作为考证学的反动,逐渐研究起批判实际政治的公羊学。不过,一直到清朝末年,公羊学并未能取代考证学而成为学问的主流。
当时公羊学的泰斗是刘逢禄。龚自珍是刘逢禄的门生,同门的英才魏源也是宣南诗社的同人。鸦片战争的主角林则徐,以及可以说为鸦片战争起点火作用的黄爵滋,都是该诗社的同人。
据龚自珍的年谱记载,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四月九日,于花之寺会诸友观赏海棠花。这次聚会是徐廉峰和黄爵滋召集的,有魏源、朱椒堂和潘曾莹、潘曾绶兄弟等十四人参加。这一天大概商谈了结社的问题,因而五月诞生了宣南诗社[;据近年来的考证,宣南诗社成立于1814年。——译者注'。
据魏源的年谱记载,五月的聚会除了上述朋友之外,还有林则徐、张维屏等人参加,会上成立了“宣南诗社”。并互相以诗唱酬。另外,六月二日龚自珍将同人邀集到龙桥寺,举行了酒会。
当时正是公羊学的泰斗刘逢禄去世的第二年, 所以也可能商谈了刊印恩师遗稿的问题。这件工作决定由魏源一个人来承担。
林则徐虽:喜欢社交.但他没有参加宣南诗社成立前的花之寺的聚会。他暂时在故乡福建服父丧,这一年的四月才回北京。四月九日赏花时,他可能还没有抵达北京。
宣南诗社的同人都是当代的英才。在他们聚会的席上,不可能只是诗酒应酬,同人中既有龚、魏这样公羊学的双璧,也有象林则徐、黄爵滋等那样充满朝气的官吏,不难想象,在他们中间会谈论“衰世”的问题。
“这样下去行吗?”
“一定要想办法!”
“那么,想什么办法呢?”
公羊学的特点是,排除抽象的言词,进行符合实际的考察,所以他们肯定会作以上的交谈,议论种种改革现状的办法。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同人在结社当时的年龄和地位。
林则徐,四十六岁。因父亲去世,辞官眼丧。在这以前任江宁(南京)布政使,宣南诗社成立三个月后,任湖北布政使.离开北京。各省的长官为“巡抚”,巡抚不仅管行政,而且掌握军权。巡抚的下面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前者负责一般行政和财政,后者辅佐司法,相当于副省长。在宣南诗社的同人当中,他的官位最高。
龚自珍,三十九岁。前一年刚中进士。曾被任命为知县(县长),因不愿去地方工作,留在北京担任原来的职务——內阁中书。中国的县比日本的县要小得多,大体相当于“郡”。内阁中书是从七品官,林则徐担任的布政使是从二品官,叮见他们的官位相差很大。
魏源,三十七岁。跟龚白珍同样是从七品官的内阁中书,但未中进士。当时他作为公羊学者已经名声很高,但中进士却是在十四年之后,那时他已经五十一岁。
黄爵滋,三十八岁。翰林院编修。他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三十一岁时中进士,未去地方工作,进入了翰林院。在中进士的人当中,成绩优秀者才能进翰林院,其他的人都被任命为地方的知县。可见龚自珍虽中了进士,但他的考试成绩并不佳。林则徐二十七岁中进士,因成绩优秀(在二日三十七名进士中,名列第七),在翰林院待了九年。黄爵滋在翰林院完成了进修任务后,又就任编修。这个官职虽不过是正七品,但作为步上青云的阶梯,等于是未来的远大前程有了保证?
由以上叮以看出,在宣南诗社成立时的同人当中,具有向皇帝上奏文资格的只有林则徐,但他在北京仅待了三个月就去厂湖北。所以,宣南诗社的同人们虽然在大谈政治,而他们的意见并不能反映到实际的政治中去。他们在那里不过是在进行政论的训练,有时练习练习奏文的文稿而已。
关于录用官吏考试的“科举”制度,宫崎市定先生写过一部专著(《科举》,收入《中央公沦新书》)。
通过府试、乡试等几层艰难的考试及格,即成为举人。只有举人才具有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的资格。会试及格才成为进士。每次会试有上万的举人参加,中进上的只有二百人左右,这道难关之难过是完全叮以想象的。
道光年间科举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年岁最大的军机大臣曹振镛的性格,除了要求通晓四书五经之外,其重点是放在要求认真写字上面。据说:“遂至一划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叮见拘泥于文字的书法甚于对文章内容的要求。
第8节:宣南诗社(2)
当时的各种书籍中也有记载这种情况的文章。如:“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燕下乡脞录》)“举笔偶差,关系毕生之荣辱。”(《春冰室野乘》)
考生和官吏都全神贯注于书写端正的楷书,虽一点一划也不能疏忽大意,政策或文章的理论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所以,写不好端正楷书的人,不管具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也很难考中进士。中不了进士,这在当时就意味着堵塞了当高级官僚的仕途,登不上政治的舞台。
作为学者,魏源或龚自珍都要比林则徐更为杰出。但林则徐二十七岁就以优秀的成绩考中了进士。而龚自珍三十八岁,魏源五十一岁才中进士,其成绩都未达到能进翰林院的水平。
龚自珍和魏源都留下了笔迹,他们的字确实很难说写得好,虽然不能说十分拙劣,但确实有不少毛病。他们很难通过最重视书法的考试,不是没有原因的。
科举的考试,对于象林则徐那样循规蹈矩的正统人物是有利的,对于象龚自珍那样感情用事、艺术家风格的人物则是一大难关。人们所渴望的“破格的人材”,首先就会被录用官吏的考试刷落下去。所以人们说道光年间的政界情况是“厌厌无生气”,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一旦中了进士,就要终生把当年会试的考官尊之为“师”。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中的进士,当年的考官就是那位楷书迷曹振镛。看一看林则徐的日记,就可了解他对这位老师是衷心效劳的。
当时的派阀和人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由这种禺然的因素来划分的,并不怎么考虑思想或抱负。不过,宣南诗社并不是同人们偶然的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