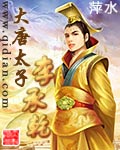大唐诗圣-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卿平在一旁问道:“那你找到白鹿了吗?”
张果老沮丧地摇了摇头:“我用的术法追踪,知道它就在这时附近,但却不知道具体在哪里。”
卿平对张果老说道:“借一步说话。”
张果老会意,从狩猎队中脱离出来,三个人驱赶坐骑来到大树下,纷纷跳了下去站在地上。
卿平在张果老耳边低语数句,张果老的脸上瞬间眉开眼笑,连连夸赞道:“姜果然是老的辣,找白鹿还是要靠你啊。”
“白鹿说让你帮忙,你帮不帮?”
张果老一拍大腿道:“当然包喽,帮完之后我就可以红尘潇洒自在行了,想想就开心。”
“那你想好怎么配合它的表演了吗?”杜蘅问。
“放心吧,我的白鹿可是非常聪明,非常听话的。”张果老拍了拍驴子的背,说道,“去吧,去找那头白鹿。”
白驴“昂——昂——”叫了几身,撒开四蹄就跑了。
“刚才你不是说找不到白鹿的具体位置吗?那这头驴子能找到?”杜蘅奇道。
卿平说:“我刚刚收了白鹿送给我的一撮毛,我把它放在驴子的铃铛里了,它嗅着这个味道就可以找到。”
原来如此,杜蘅心想,以后八仙的坐骑驴果然也是一头非同凡响的驴子,像他自己就没有这个能够闻一闻对方的气味就找到对方的功能。
玉真公主也换上了骑装,和一些女性骑手在山林中纵横,看到张果老牵着驴子站在道旁,就过来问道:“怎么你不找白鹿了?是想认命等着娶我吗?”
张果老哼了一声:“你可别得意,白鹿已经找到了。”
玉真公主笑道:“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张果老说完吹了一声哨子,只见刚刚消失不见的白驴又跑了过来,一头冲到他的怀里。
张果老摸了摸白驴的脑袋,夸奖道:“乖。”
这个时候众人的目光都投向白驴后方,只见一团柔和的白光从那幽暗的树林里闪了出来,紧接着一头浑身散发着瑞气的白鹿,出现在林地之间。
玉真公主看到白鹿眼前一亮,她也是修道之人,只消一眼就知道这是一只货真价实活了千百年的灵鹿。
她命侍女拿来一罐药草,倒了一些在手里,朝白鹿摊开手掌。
卿平之前说的没错,玉珍公主那里果然收集了一些非常好的药草,而这些都是对于白鹿修炼灵气非常有益的东西。
白鹿用鼻子嗅了嗅,心里已然乐开了花,表面却非常矜持地迈着优雅的步伐,缓慢地踱了过来,故作漫不经心地嗅了嗅玉真公主手上的草药。
玉真公主见他不感兴趣,就又放了几枚红果子在草药上,催促道:“这是给你准备的,你放心吃吧。”
白鹿这才开心地在玉真公主的手掌心里吃了起来,它在山里呆了好久了,吃的都是寻常的果子和野草,这是它很久之后难得再一次吃到富有灵气的药草和鲜果,心里对于未来的生活很是满意。
“你愿意做我的坐骑吗?”玉真公主一边摸着白鹿背上的毛,一边问道。
白鹿乖巧地点了点头,玉真公主也很高兴,看来,主人和坐骑达成了完美的共识。
于是白鹿就伏低身子,让玉真公主坐在它的宽阔的鹿背上,驮着公主走在狩猎队的前面,昂着脑袋,趾高气扬。
玉真公主俯视着坐在白驴上的张果老说道:“我言出必行,既然已经找到白鹿,那我就回去向哥哥进言撤销赐婚,现在你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了。”
“那就多谢公主了。”张果老朝她拱了拱手,又转身向卿平和杜蘅告别,“我又要游历名山大川去了,以后有缘再见。”
“等等。”杜蘅叫住了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的坐骑。”
“问吧。”张果老拍了拍白驴。
“嗯……这位驴前辈,请问你知道我的原型是驴子吗?”
白驴看着他,片刻后眨了眨眼睛回答:“不是。”
当真是言简意赅。
“既然不是,那你之前还叫我小后生,我还以为是你是我的前辈呢?”
白驴斜了他一眼:“你这就是想当然了,我这么说是因为大家都是坐骑,你年纪比我小,修炼得又比我晚,当然就叫你后生了,又不是说你和我一样都是驴子。”
“那前辈知道我到底是什么动物吗?”
白驴只回了他一句话:“天机不可泄露,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寻找。”
杜蘅见没有问出什么所以然来,只好又向玉真公主询问:“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见到一种叫做騧马的马?”他也好去确认一下那马到底长什么样,和自己是否有相似,如果是同一种类的,对方看到自己应该能认出来吧?
“騧马是来自西域的一种非常名贵的马匹,在夷城这个小地方是找不到的,我的狩猎队也也没有。”玉真公主好心地对杜蘅讲解,“这种马一般来说都是皇家才能拥有的,长安城的宫殿里肯定是有的,洛阳作为神都也养着几匹騧马,这里离洛阳更近些,你可以去洛阳看一下。”
“多谢公主指点。”杜蘅暗暗动了心思,有机会要再去一趟洛阳。
在他和玉真公主说话的时候,张果老已经谈着道情,唱着欢快的歌声,倒骑着毛驴,缓缓走在山道上了。
杜蘅目送着张果老骑驴的身影渐渐远去,只听那张果老唱的是:
“世人都道神仙好,我在人间赛神仙,名山大川都走遍,潇潇洒洒几春秋。”
伴随着张果老的歌声,玉真公主的狩猎队也朝另外一个方向自行下山了,一轮火红的夕阳悬挂在枝头,周围雾霭渐起,是该去寻李白他们了。
卿平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山头:“就在那边。”
玉真公主出手很是大方,几匹骏马和全套猎具都送给他们了,没有准备要回来的意思,杜蘅他们骑着马,很快就来到了山岗上。
只见李白、杜甫、高适三人都骑在马背上,正排成一排,眺望着西天无比辉煌灿烂的落日。
夕阳下可见山下的夷门城池,车马依稀可见。
见三位诗人看得入迷,杜蘅不由得压低声音问道:“他们在看什么?”
“在看这大唐盛世江山。”卿平回答。
杜蘅想起了他从历史、文学科普读物上看过的那些未来,在安史之乱之后,曾经一起骑马射猎的好友,走上了三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有些人分道扬镳,有些人形容陌路,有些人依然保持着往来,多少有些令人唏嘘。
一句这个时候还没有问世的名句突然跃入杜蘅的头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
作者有话要说:为什么大家都猜骡子啦,我还没准备彻底搞笑,捂脸
下一单元胡璇舞
第48章 胡旋舞 一
那天下山便晚了,因此就在一山脚下住宿了一宿。高适说家中备上了美酒,于是几人又返回了睢阳城。
回到睢阳,不料高适家却有一个小少年正在等着,这小少年长得跟杜甫有几分相似,脸蛋圆圆的,看起来还未脱孩子气,十分清秀可爱。
杜甫看到这小少年在门口等着,连忙翻身下马说道:“阿丰,你怎么在这里?”
被唤作阿丰的少年揉了揉眼睛,说道:“阿兄,你总算回来了,我给你带了一封家书。”
原来这名少年便是杜甫的三弟杜丰,今年只有十一岁。杜甫先前传的家信,说自己去梁园遇到了高适云云,杜丰恰好经过此地,便寻到了对方家中。
杜甫慈爱地摸了摸杜丰的脑袋,问道:“你特地跑到这里来,可是家中出了什么事?”
杜丰乖巧地点了点头:“阿兄的外祖母病重,那边盼你早日回去。”
杜甫的父亲娶了两任妻子,杜甫是第一任妻子的唯一孩子,下面的四个兄弟、一个妹妹都是继室生的。
不过杜甫和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感情和亲兄弟一样好,杜甫作为大哥平时在诗歌里也经常提到他们,留下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样思念兄弟的名句。
听说自己的外祖母病重,杜甫也没有了在外游玩的心思,马上准备向高适道别。
高适说道:“那就吃了便饭再走吧。”
吃饭的时候毕胜突然对杜甫开口说:“先前我随你前去,就说了等你回去洛阳,要将我带去见见你的外祖母,这话还算数吗?”
“当然算数。”杜甫点了点头说,“我肯定是要将你带回去的,说不定外祖母见到你还很高兴。”
毕胜点了点头,就独自走出去了,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
高适对杜甫说:“你回去的路途上要注意安全,不要为了急于赶路搞到车马疲惫,要是生了病可就不美了。”
“多谢达夫兄关心,我心里有数。”杜甫回答。
李白将杯中酒饮尽了,豪迈地说道:“既然高兄不放心,那不如我陪杜甫回趟洛阳吧,反正我在外面,总归走到哪儿都是一样的。”
杜甫面露喜色,不过嘴上还是推脱:“如此,岂非太麻烦太白兄了?”
李白拍了拍杜甫的背说道:“你我之间说什么麻烦。”
杜丰正在吃饭,听到他们之间的动静,突然抬起头来说:“这位就是李太白吧?我在家的时候可没少听阿兄夸赞过你的诗句,清新如庾开府,俊逸似鲍参军呢。”
杜甫猛然被弟弟揭了老底,脸色一红,略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李白倒是非常淡定,朗声大笑道:“原来子美对我的诗歌评价这么高?那我就笑纳了。”
临行前,高适又给他们塞了一些盘缠和干粮,将他们送到城外。
虽然说了不要旅途劳累,不过心系外祖母的杜甫还是加快了脚程,比杜丰来时更快地进了洛阳城。
进城后,杜丰陪他们来到宅院门口,就和杜甫告别了,因为那并不是他的母家,他暂时去探视添乱了。
此时天气已经是冬天,洛阳城这几日没有太阳,颇有些阴了,杜甫外祖母李幼安的房间就安排在一处向阳的院落里,外面几圈修竹,因为病人怕风,所以窗户都紧关着,房间里有些昏暗,点燃了几盏灯,弥漫着浓浓的药味。
杜甫只带着杜蘅两人走了进去,只见已经白发苍苍的李幼安躺在榻上,盖着一条厚厚的棉被,皱纹已经爬满了被岁月侵蚀的脸,已经全然看不出杜蘅以前在毕胜的记忆里看到过的那张令人怜惜的少女的面庞了。
“外祖母,我是杜甫,我来看您了。”杜甫跪坐在榻前,握住了李幼安干瘦如柴的手。
躺在床上的老人眼睛略微张大了一些,露出了一些光亮,似乎想要将面前的人看得清楚。
“是杜甫啊,听说你这几年一直在外面游历,难得回来看我。”
“是啊,我一直在外面走南闯北,未能在您面前尽孝。”
李幼安拽紧了杜甫的手:“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一直以来也没有能够照拂你的仕途,你的母亲去世的又早,这些年来,看着你渐渐长大,我就很开心了。”
杜甫动情地说:“外祖母,我这次带了一个故人,你看看认不认识他?”
说话间,悬挂在杜甫腰间的筚篥,弥漫出一道紫烟,身穿紫色华服的毕胜出现在榻前,他坐在榻边,看着躺在床上已经年华不再的李幼安,用袖子挥了挥,似乎是要将那些缠绕在对方身上的病气驱赶掉一些。
“你是谁?”李幼安看着眼前的人,她虽然没有见过这个人的面容,却觉得对方的气息令她分外熟悉,那是一种令人非常怀念又安心的感觉,使她想起了很久很久之前的少女时期。
我曾经有一个时候也在对着什么不停地述说自己的苦闷,而后来那个聆听者去在岁月中却不知所踪。李幼安这样想着。
“我是毕胜。”毕胜的声音也有些颤抖,“你还记得当年,你吹奏过的那支筚篥吗?”
李幼安伸出颤抖的手,想要去摸一摸对方的衣袖:“是你?难道乐器也能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