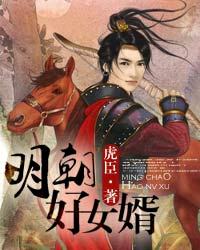穿到明朝考科举-第1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人捡了处人少树稀,有干净大石头的地方歇下,把马系在身后一株大树上,拿了些黑豆喂马。
从他们坐的地方放眼望去,正好能看到卢师山、觉山两处景致,天空又是秋天特有的明净锃蓝,看得人心胸开阔。崔燮站在大石块上远眺山景,念了一句“西山朝来,致有爽气”,感觉自己仿佛也有了王子猷一样的名士气息。
谢瑛从马鞍旁的袋子里取下一坛酒,一盒糕点,在地上铺了块织满彩纹的厚实毡毯,叫他坐下来吃点儿东西。
看着谢瑛又铺毯子又拿东西,崔燮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搓着手说:“我以为到寺里什么都有了,就没准备。早知道要野餐,就叫人做点吃的带来了。”
谢瑛摇了摇头:“倒不用在野地里待那么久,我只是想着到重阳日咱们没机会见面,提前带你出来爬爬山,喝菊花酒、吃重阳糕,也是个过节的意思。”
他倒出两杯微带碧色的酒,打开盒子,露出满满一盒糕点,举杯对崔燮说:“没叫人做重阳糕,只是些普通糕点,我记着你爱吃这几样。倒没叫人仿你家擅做的那些奶点心,怕你在家吃絮了。”
喝了酒便能驱赶寒气,暖暖身子。
两人举杯相碰,满饮了两杯。谢瑛还待给他倒酒,崔燮奇道:“往常你都不叫我多喝,今天居然开酒禁了?”
开禁还不好么?谢瑛斜欹过身子来,拿脸颊贴了贴他的脸,觉得还是凉凉的,就又给他倒了一杯,说道:“天气凉,给你多吃几杯暖身的。这是拿百果酒蒸的素酒,吃了也不怕冲撞禅寺,吃醉了就在寺里睡一觉,醒了酒再家去。”
嗯,反正平坡寺就是后世的香界寺,他从前去玩过,也没什么可看的。
崔燮吃着点心过口,又喝了一杯酒,提起壶来给谢瑛倒上,借酒遮脸,笑嘻嘻地对他念起了淫诗:“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谢瑛果然不知道这诗是“淫奔之诗”,以为他就是撒撒娇,诉诉相思,便低头喝了他杯里的酒,握着那酒杯和他的手指说:“你这书倒不白念。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你这都会拿诗经代自己的话了,也算是学透了吧?”
崔燮转了转酒杯说:“还不算学透,我也才只读了朱子和毛诗的注释,还有许多理解不深刻的地方,得多听先生的讲解。辟如这首《采葛》,其诗就是见葛起兴,发本心深存之情志。女子以有所思之心与其当时采摘的萧葛艾等外物相感,神理凑合,其情思浡然而兴,故作诗以咏之。”
诗里写的本就是遍地皆是的野草,连这山顶上都能见着,只不过如今天气渐寒,这些草还没经霜就已经衰败了。若早一个月、半个月的出来,只怕还能见着正开花结果,生机炽盛的艾草呢。
他随意扯了几根半黄的枯草过来,也不管是不是萧草,在谢瑛手上绕了几圈,笑微微地说:“我也是有所见而起兴啊。”
见人起兴也是兴啊。
谢瑛反手握住他的手,把那草茎一半儿缠到他手上,捏着那只叫枯草衬得越发白净修长的手说:“我读论语时见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我们武学里不读经,后来忙着办差,也没处学这些,难得认得你这么个秀才,你给我仔细讲讲,什么叫作‘兴’?”
……大哥,你要听的是哪个“兴”?
咱们俩一个半月没见面了,见面了不抓紧时间吃喝玩乐,还要讲《诗经》,这还叫约会吗?
崔燮感觉颇有些悲愤,恨不能撩起他的裙子教教他什么叫“兴”。
谢瑛看他一脸不情不愿的样子,知道这时候还要讲经不人道,可是叫他又念诗又上手地调戏了这么半天,再不讲经就真要“人道”了。他摸着崔燮微烫的脸颊,安抚道:“你给我讲讲,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就山下平坡寺的故事,如何?”
这怕不是把他当六岁哄了吧?讲经还不如起来练个剑呢。
崔燮老气横秋地叹了一声,无奈地讲道:“朱子释兴为‘感发志意’,国学先生所解,是说‘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兴便是胸中一股振发激扬之气,先王采诗以教化百姓,便是为了兴其胸中之气。
“兴本于情。作诗时心中有待发之志,而外物正含蕴天地之理,其理又恰与我心中之志相合,情理凑合,心与物交感,则眼前之景自然化作文章妙句……”
眼前一个正该跟他的“有识之心”相取的佳人,怎么就不能好好的“相值”“相通”,非要听他讲文章呢?
谢瑛盘坐在毯子一角,让他把头搁在自己大腿上,躺在那里慢慢讲书,自己拿着果酒时不时喂他一口。看他说的慢了,像是酒意要上头时,又拿着萄葡、海棠喂他,帮他解酒意。
他的火力比崔燮壮,这日子还只穿着几层单衣。拿东西时,宽大的袖子在崔燮脸上、胸前不时拂过,闹得他脸上发痒,忍不住抓住那只手,哑声说:“你把袖子卷上去,再刮来刮去的我可要撕了。”
谢瑛低头看了一眼,看见自家袖子半堆在崔燮脸上,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右眼和嘴角。眉眼是虽微皱着,嘴角却含着笑,伸出手来摸他的脸。
谢瑛低了低头,好叫他够着自己,任由他在自家脸上胡乱划拉,挽起袖子劝了句:“莫闹得太厉害,待会儿要去庙里,小心冲撞了神佛。”
崔燮惊讶地问了一声:“谢兄竟信佛?是居士么?”难怪他爱情观这么古板,还非得不学习了才能搞基……他原来还以为是因为明朝人就保守呢!
谢瑛笑道:“也就是见什么山上什么山,遇什么庙拜什么庙吧。从前随侍在宫里的时候听过继晓大师、李监丞他们讲佛道教旨,都觉着好。皇爷也讲究三教一体,我这成日耳濡目染的,自然也跟着信,不过我不如你信的诚。”
崔燮一脸问号,睁大眼看着他。
谢瑛看他这般反应,也有些迷惑:“你不是信菩萨吗?你当初给我的那张观音仿如菩萨化身,我在别处见的观音图都没那么清圣的。每到清明、佛诞、中元、新年……节庆时上市卖佛经的那个清竹堂不也是你家的?你给皇爷画的安天大会不也都画的如神佛真容落在纸上的?”
不……我只是个电视剧的搬运工罢了。
难怪大过节的,谢瑛把他带到个香界寺,还一副清心寡欲要做和尚的模样。
崔燮露出了一个悲伤的笑容:“我也只是会画个画儿,倒没有谢兄想的那么虔信。要不下回咱们还是在家里见面吧,寺里终究不大方便。”
谢瑛在他额上掸了一记,轻轻骂道:“别胡说,这样的话是可以轻易出口的?我看你也不想讲经了,索性也别赖在这里,先到寺里吃些东西,拜一拜。平坡寺是皇爷驾幸过的,里面也果然有些神异之处,咱们诚心拜一拜,也求个平安。”
平坡寺仁庙年间修过一回,改名叫作大圆通寺,不过世人都还叫着平坡寺,作诗作记时也写作平坡寺。
谢瑛记得崔燮是个没怎么出过门的人,带他进寺之后就领着他去看了敕造的碑,一双高大的古树,又进正殿看三世佛,后殿看滕胎的观音大士,侧殿看金刚……口说着不怎么信,只是听人讲讲,拜佛时都是极认真叩拜,口中念念有词,许下了不知什么心愿。
崔燮到得庙里也尊敬了许多,该拜就拜,该捐就捐,也上了几炷香烟,跪在佛前跟他一样喃喃地祝念。他也没什么野心,只希望在明朝的生活顺顺当当的,早点考上进士,早点退休……
他微微侧过头,瞟了谢瑛一眼,嘴角不知不觉挑起来,复又低下头祝愿:“顺便早点跟谢瑛在一起,不用像现在似的,出门玩都跟做贼似的。”
他低下头后,谢瑛的目光也转过去看了他一眼,神色却是深沉的多,回身默默祝祷:“……若得我佛庇佑,弟子愿捐银五百两修缮大殿。”
两人各自许了愿,都站起身来,也不须问对方许的什么,就混在香客里去了禅房,吃了顿清素的斋饭,待到过午才离开。
下了平坡山,离那寺庙远远的,谢瑛才从袖子里掏出个锦盒递给崔燮,叫他收着。崔燮一看便觉出眼熟,摇头笑道:“这是我家出的眼线膏盒子,谢兄怎么想起拿这个给我?难不成锦衣卫里真时兴起这个了?”
谢瑛自己没涂过,也还没到能看出别人涂了眼线的高度,也摇摇头说:“这是从高家听戏时得来的,高百户说是都时兴拿它送相知的人。我知心也的只你一个,不送你送谁?哪怕你收着积尘呢,也算我的心意——你别拿回去就放到柜上卖了就是。”
高肃这眼线膏还是计掌柜送的,兜兜转转又回到他手里了。简直跟过年买点心送礼,几家来来回回地串着送,最后送回了买的人手里一样。
崔燮到底也是收了礼,有点高兴,把盒子往袖里一揣,说道:“罢了,我也不管这是什么东西,只当是你送我个小件的藏品,回头搁柜子上摆着就是了。”
谢瑛笑了笑,目光落在盒盖上,欲言又止,终究只说:“咱们回去吧。”
他该做的都做了,放下心只想回去,崔燮却才想起来:“说好了你给我讲故事呢?怎么从庙里逛了一圈回来,你倒不讲了?”
谢瑛笑道:“不曾诓你。只是这故事事涉平坡寺,当时在寺里不好讲罢了。方才带你看的金刚你可记得么,是不是觉得比别处的造像要新?”
好像是吧,他当时哪儿还顾的上看佛像,没注意啊。
谢瑛回首看着佛寺,脸上笼着斜晕,竟带出了几分虔诚庄严的神色:“这是早几年我还没当上卫所千户,刚开始随驾做仪卫时,曾随侍万岁爷驾幸本寺。带你看的那个金刚那时是个黑面金刚,万岁见而笑曰:‘此似火里金刚’。后来那金刚像一夕之间便遭火焚,如今这个像是新塑的。”
明宪宗真非凡人也!
这个乌鸦嘴……太服气了,不愧是天子!
崔燮实在不知说什么好,只能闭嘴惊艳。谢瑛倒是一派至诚之色,感慨道:“也不知是金刚感天子之旨而焚此像,还是皇爷身非凡人,能前知佛像将坏之事。”
不过能出这样的异事,想必这寺就是比别处灵验,他们在这里拜过佛、许了愿,终究会有佛菩萨保佑,许他们心想事成的。
两人并辔在城外跑了一路,进城后才各自分开回家。崔燮袖着约会的礼物回到院里,进了门谁也顾不得见,先抱着盒子在床上翻滚了一会儿,闭上眼默默想象着谢瑛在家里悄悄关着门画眼线的模样。
其实男人也化妆啊,现代的男演员上戏、做节目都要化妆,他们国学的同窗们也有带着妆上学的。锦衣卫这么时髦的人物,画画眼线也不算什么大事么?
谢兄画了肯定比那些人都好看。
他躺在床上,摸着那盒子幻想了半天,又打开盒子,拿出盛眼线膏的小瓷盒,想看看有没有用过。拿盒子时,化妆刷和一张纸就飘了下来,直愣愣地砸在床上。
他们为了省成本,当初是用薄纸印制说明书的,这纸怎么看着又厚又重的?莫非是谢兄写了情书,不好意思当面给他,夹在这盒子里了?
崔燮心里一激灵,猛地坐起来,捡起那张纸展开来看——
纸上并无一个字迹,唯独画着一双眼睛,画的不甚熟练,却能看出几分眼熟的神韵来。
崔燮双手托着纸,盘坐在床上来回看了不知多久,满脸都是笑意。他把那张画叠起来收进盒子里,藏进了书箱最底层,而后翻身下床拿了铅笔和一沓双层厚纸,用木板支成画架,慢慢打稿。
画他的眼睛,不就是想看见他的意思?不能看见真人,看着画也能聊慰相思嘛。
这副画反正也是下回见面时才能给他,因此崔燮也不着急画,光草稿就改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