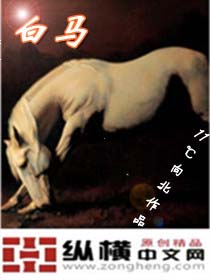白马-第29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位将军身陷营口,只身前往营口搭救,未来得及收到圣旨,公孙将军说这话,岂不是让我家大人寒心?”
闻此,冰冷如霜的公孙瓒身子一颤,愧疚由生!
“大人之过救驾来迟,那也因为未收到随行护驾的旨意!”瞧见公孙瓒愧疚之色,麴义压制住自己的愤怒,坐回原位,压低声音,回应道:“不过,我想即便大人收到天子指令,也定会为兄弟情谊而放弃君臣之恩!”
言罢,麴义扭头不语。
闻此,公孙瓒却骤然起身,背对着麴义,身子微微抖动,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说大人是叛军,谁信都可以,恕我冒昧,唯独公孙瓒将军不可!”
麴义目光直刺公孙瓒的背影。
听闻此话,公孙瓒转回头,不明的瞧着麴义,为何有这么大的反应。
见公孙瓒不明,麴义开口解释道:“昔日广宗城下,如果不是大人只身入城,先斩张角的头颅,怎会有两位将军破城之功?”言外之意,公孙瓒和刘备不仅承皇甫岑人情,而且张角也是死在皇甫岑手中。
“你——说——什——么?”
公孙瓒几乎用尽全力在问这一句话,不过不用麴义回答,公孙瓒就能想明白,昔日在广宗城下见到的那熟悉的背影,就是皇甫岑,就是皇甫岑杀了张角,还把破敌之功让给自己兄弟!
“大人他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兄弟的事,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师的事!”
言至此处,麴义已经平复不了,胸中的那股暴戾之气,愤然起身的观瞧着面前的公孙瓒。
二人的交谈,一下子停顿了。
许久后,公孙瓒才背对着麴义,问道:“说说经过吧!
“大人闻言天子征调,从卢龙塞连夜赶路,途中受吕布伏击,要不是有义士相助,恐怕早已经身死敌手。幸我河东上下有高人指点,大军急速南下救驾,却被黑山军阻截此处。待叛贼里应外合,孙将军调往城外,收伏击,信都城内,王芬招募死士借机动手,尚书卢公本是受我等所求,提醒天子小心,却遇贼起事,卢公奋力死战,大人来后,见卢公身死,当场昏厥,而叛军见事情败露,临死反咬大人一口,时,大人昏厥,无可否认!”
言罢,麴义把手中佩剑狠狠摔倒几案上,似泄愤一般!
“嗯。”
背对着的公孙瓒深吸一口气,手上不自觉的握紧腰下佩剑,事情已经很明了,分明是有人陷害!更可气的是,天子居然会相信,而且,整个被救的官员们,没有人敢为将军求情脱困,如此这般,怎叫他不生气!
一气说完后,麴义抬起头颅,抑制眼中即要流出的泪水,愤恨的回应道:“我们一直怀疑,在天子身边有人串谋!”
“串谋,为了什么?”
公孙瓒转回身,语气好了许多的问道。
“先是要篡改天命,眼下却要置大人于死地!”
麴义回应道。
“嗯。”
公孙瓒点点头,整个凌乱的脑海已经抽丝剥茧,明白一切过往。
“现在,只要将军南下洛阳,奏明圣上一切经过,证实大人身去营口,并未接到圣旨一事,自然可以断定大人无罪!”言罢,麴义冲着公孙瓒深深鞠躬,低声道:“他们意图诬陷大人勾结黑山军谋反,只要将军提及张角旧事,自然解惑!一切……”言到此处,麴义抬头望向公孙瓒,低声道:“皆望将军!麴义,感激不尽!”
言罢,麴义撩衣襟跪倒。
公孙瓒连忙上前扶起麴义,愧疚道:“何来所望,老二之事皆因伯珪而起,伯珪怎能坐视不理。”说到这里,公孙瓒佩戴好甲胄,转回身,坚决的回道:“如果我公孙瓒再有推辞,就不配做他皇甫岑的兄长!”
“好!”
麴义冲着公孙瓒拱拱手。
“我这就南下!”公孙瓒转回身冲着麴义拱拱手,道:“告辞!”
“告辞!”
……
朝廷决议压后,等待公孙瓒南下,再决定一事,迅速传遍了洛阳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每个人都在关心着皇甫岑的生死一般。这不能说是洛阳百姓太过关心皇甫岑的生死,而是因为皇甫岑确确实实关乎着大汉百姓,影响着大汉。
皇甫岑初任属国都尉,便在昌黎城立不势伟业,已经功成名就,成为大汉的代名词。
当初的影响也不过在辽东而已。
而后,皇甫岑怒杀公綦稠,八百壮士齐卸甲,事后初任河东,造福一方。就更显得皇甫岑文治武功,德才兼备!
而后的影响,一下子串联到北地的每一个角落。
之后,大汉风起云涌,天色渐变,各地叛乱蜂拥而起。
是皇甫岑一手剿灭了“蛾贼之乱”;是皇甫岑一手镇压了“匈奴之乱”,连带着收拾了中部鲜卑;也是皇甫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独闯辽东,令“义”字犹存汉人心间。使汉人不曾忘记,他们安生立命的根本,便是“雄炯气昂昂,慷慨赴国难!”。
有了,皇甫岑,整个大汉的气概便不一样。
皇甫岑如今下狱,什么原因不谈,但是洛阳百姓却没有谁愿意看到这一幕。
一个保家卫国,为大汉出生入死的将军就这么陨落,整个大汉却再也看不见,皇甫岑的身影,这是何其的无辜,何其的恼人怒!
聚集在洛阳的豪杰义士,一瞬之间便多了起来。
夏育、尹端的队伍人数不多,几百之重,并未把湟中义从全部带来,但这几百人却已经是湟中义从中能挡万军的精锐!他们刚刚走到孟津,便听到了冀州刺史王芬意图谋反,皇甫岑踉跄下狱的消息。他们知道天子一定会回洛阳再做决定,随即带着身旁的部曲,就势回到了洛阳,偷偷地找了两个院落,住了下来。
白天的时候,查探洛阳的消息。
夜晚的时候,摸清廷尉府和天牢的概况。
只为了,皇甫岑被押送回京后,没有退路之时,偷劫天牢!
“将军,探查好了。”
湟中义从之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汉人凑到夏育、尹端的近前,开口道。
“嗯。”
夏育点点头,挥手湟中义从下去准备。
“是不是在等一等?”
尹端凑到近前,问向夏育。
“还等什么?”
夏育不明的问道。
“我总觉,这事是不是太简单了,咱们这么办无一不是在不打自招!”
尹端抬头看着夏育。
夏育却转回身,凝视尹端,回应道:“其他的事情,我不清楚,但是我夏育却清楚一件事,昏君是认定了皇甫岑,他现在绝不会放过皇甫岑。就像……当年,昏君逼死段公!”回忆起往事,夏育的眼睛之中,全是泪水,停滞了一下,夏育拍案而起,转身道:“这种事情,我夏育绝不会让他再上演!”
“呃。”
见夏育提及旧事,尹端嘎嘎嘴,不言。
对于太尉段颎一事,他是无能为力,只有闭嘴不言。说多了,恐惹是非,毕竟他还是张奂的部将。
“走!”
夏育下定决心,背对着尹端,低声喝道。
尹端抬抬头,终于忍不住的说道:“我们是不是联络一下臧旻,看看他是怎么想的?毕竟……”凉州武将,三明之下,便是皇甫嵩、董卓、尹端、田晏、夏育、臧旻,说起通晓文墨,只有臧旻学识最深!尹端之意,是想听一听臧旻的意见,当臧旻不在洛阳。而夏育素来同臧旻不合,这事谁都知晓,臧旻出身是凉州武将之中唯一一个山东士族,算不得正宗的西凉武将。但他常年随着段颎征战,久而久之,便化为段颎一系!
“还等他?”夏育深知尹端所想,鄙夷道:“明哲保身的家伙,连董匹夫都不如!”
言罢,夏育带着一众人马便踏月而走。
尹端嘎了嘎嘴,最后只好随行而去,生怕,夏育干出什么恼人的事情。
一行几十人,戒备、探哨、放风,各行其事。
轻车熟路间,便赶到了天牢附近。
夏育冲着一旁手急脚快的湟中义从使了使眼色,示意他们把巡逻护卫的侍卫们调走。又冲着湟中羌挥一挥手掌,示意他们去解决掉门口守卫的两个侍卫,毕竟面生,以后事发后,羌人面孔也为皇甫岑开脱了责任。
湟中义从毕竟是常年随军的老人,短短几个动作之后,便彻底的收拾了面前几个家伙。
夏育又派两个汉人拖走那两个侍卫,换上他们的衣装,站在门口守卫。
看似复杂的一系列动作,短暂之间便彻底的解决。
夏育同尹端留下一部分湟中义从,其他人随着他们二人冲入天牢之内。
“谁呀?”随着牢房的门板被叩响,里头传来牢头不耐烦的低吼声,道:“大半夜还不让人睡觉,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见此,夏育清了清嗓子,尖锐吼道:“滚开,快把门打开,如果天子怪罪下来你能担待的起,咱家还担待不起!”夏育整个嗓音都是学着太监模样。
一旁的尹端都忍不住的笑了笑,夏育精灵古怪,近五十的年纪,竟然可以这么搞笑!
里头的牢头似乎听到了这一嗓子吓得不轻,急忙哆哆嗦嗦的打开石锁,并不时的求饶道:“公公!不知道公公大驾光临,小的这就打开门锁,公公……稍候!”
随着他的回应,门锁哗啦啦的打开!
里头刚刚冒出一个人头模样的家伙,湟中义从在没有夏育的指挥下,迅速蹿入,并一掌击在那牢头的后脑,那牢头甚至都来不及看清楚面前之人,便昏厥过去。
其他湟中义从在牢里其他官员尚未反应过来之际,急速的制服其他人,目光压低,环视着周围众人。
天牢之内,被关押的只有几个人。
仿佛这一切都是为皇甫岑所建造的。
夏育没有见过皇甫岑,一把拉过尹端,带着黑布,低声道:“哪一个是?”
他们做事隐蔽,却并未开口言明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天牢之内同被关押的许攸、周旌一下子惊醒。
周旌一喜,以为是谁来营救自己等人。刚要开口说话,便被一旁的许攸拉住手臂,凝望眼前之人,询问道:“你们是谁?”
闻言,夏育看向许攸。
却见尹端摇摇头,目光扫视一圈后,停留在一座偏僻的角落,直视躺在角落里的那个人。目光停留在那人身上,心中却是突兀的一颤,没有想到,几年未见,皇甫岑的竟然混到如此光景,周身上下虽然不见刀伤疤痕却只见他浑身衣衫褴褛,发髻松散,哪有昔日所见的风流倜傥模样。
“他是?”
夏育一惊,回头问道:“那么他们呢?”
听两个蒙面人对话,许攸一惊,带着手镣脚镣的他向后一退,警戒的望着面前这股强人。
而旁的周旌也是一惊,怒视面前来人,如无意外,面前这些人是来营救皇甫岑,而不是他们的救星,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以黑布蒙面,看不出是谁,但看身形,膀阔腰圆,看摸样便像是从军之人,但偶尔发出声音却带着羌氐口音,不是白马义从,白马义从之中的胡人,大多数是乌丸人,或许会有几个匈奴人,但绝不会有羌氐口音。
这群人,究竟是谁?
周旌同许攸目视几眼,各自不言。
尹端瞧了瞧,低骂道:“还能有谁,不过就是那些真正的反贼。”
“就是他们诬陷?”
尹端一说,夏育便明了的看着他们,愤恨的瞪了瞪,冷声道:“杀了他们!”
言罢,便有湟中义从提刀来取许攸和周旌的性命。
尹端看了一眼夏育,道:“先不着急动手,问过仲岚后,再做决定不迟!”话罢,尹端随着夏育朝着皇甫岑走来。
此时的皇甫岑也已经发现了这突如其来的一股强人,同样,来人交谈不多,又以黑布蒙面,察觉不出他们是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