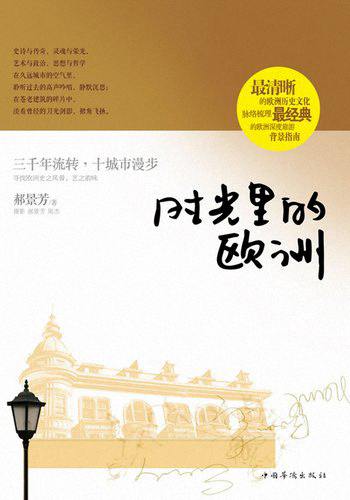时光,若能重新来过-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报纸上的那个男人这样年轻,身材修长,与一个高挑的女子一道从酒店出来,形状亲昵。
“假的。”乔远川忍不住笑了笑,年轻的女孩子总是爱关注这样的八卦。“阿原不是这种人。”
晚餐非常愉快,因为近距离的接触了偶像,林荟文有些羞涩,也有些紧张,只是徐泊原很快就离开了,一晚上都面色如常的乔远川,终于淡声问:“什么朋友这么重要?”
徐泊原在门口顿了顿,没有回答。
她却心细的发现,乔远川的手放在膝上,无意识的握成了拳。她以为他又开始疼痛,悄悄的将药递给他,可是乔远川却推开了,之间扶着微烫的杯壁,似乎在出神的想着什么,而身形这样僵硬,令林荟文想起看舞台剧的那个瞬间。
那晚他似乎不想回家,叫了许多同事朋友,最后在半城酒店唱歌。
她有些担心他的身体,却也发现他的异常,因而也就不开口劝他。
车子掉了个头就到了酒店门口,乔远川的目光却不曾离开那一片漆黑黑的街区,薄唇紧抿,心事重重。
“喂,你怎么了?”
黑暗中,她依然能感知到空气中一种极为紧绷的情绪。良久,他才收回目光,打破沉默,“没什么。”
同事们大多都玩High了。林荟文一直盯着乔远川,但凡有人来敬酒,她便不动声色的替他挡掉。可是到底百密一疏,自己出去打个电话的时间,乔远川竟开始喝酒,大杯大杯的洋酒,眉头眨也不眨的喝掉。等她回来,他竟已经是浓浓的醉意。她又气又急,却不能在同事面前发作,手足无措的时候,打电话给徐泊原。
最后是他一把多走电话,重新拨了号码,口齿不清地说了什么,才笑着说,“他们也过。”
林荟文不敢在离开他的身边了,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包厢门被破开了。
她推推乔远川。“小舅舅来了。”
他躺在沙发上,似乎睡着了,她只能站起来,对着那个人影招招手,“这里。”
那两个人很快的走进,林荟文的身子忽然僵住了。
他看到徐泊原俊朗眉眼中浅含的笑意,他的手亲昵的拦在那个女孩子的腰侧,而那个女孩,自己见过的次数虽然不多,却印象深刻——唐思晨。
醍醐灌顶。
乔远川隐忍着说,“我希望她不要再回头,有人比我更合适…留在她的身边。”
那个人竟然是徐泊原。
她努力掩饰起震惊的目光,低头看着乔远川。
他在孩子气的沉睡,不曾见到这一幕……林荟文有那样多的问题要问,却莫名的庆幸,他没有看到这一幕。
有太多的事,在短短一段时间里发生,追的她难以思考,也难以呼吸。她看到唐思晨逃离一样出了包厢,看到徐泊原有些刻意的起身去另一个角落拿饮料,看到乔远川挣扎着起身,跟着那个背影一道离开。
在回过神的时候,徐泊原已经坐在了自己身边,他像是没发觉这里少了两个人,只是云淡风轻的抿着水。
“小舅舅……”她看到他的目光深邃如海,想要说什么,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侧头对她笑笑,知道手机一闪一闪的亮起,他低头看了一条短信,唇边蓦现温柔,“司机很快来了,你和远川一起回去吧。”
“你呢?”林荟文脱口而出。
“我去找她。”他的神色平静地不可思议,“我们也回去了。”
这一晚,她看到他咳出血,带着哭腔,颤声说:“你还好吗?”
“小丫头,别哭。”乔远川伸手替她擦去眼泪,低低地说。“我么事。”七月的盛夏,他已很少去上班,除了接受治疗,便安排他待在家中。
虽然病情的进展并不乐观,可林荟文总是很有信心,只要他的意志不消沉,就还有希望。她也有他家的钥匙,这天推门进去,偌大个房子,空空无人。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她独自一人,找遍了文岛每一处他可能出现的场所,却一无所获。
直到第二天,医生打来电话,语气严厉,询问乔远川为什么不来治疗。
她终于着慌。
纸终究包不住火。
短短的三个月,只有林荟文才知道为了保守这个秘密,自己究竟处在怎样的高压之下。她失眠数晚,终于再也坚持不住了,哭着打电话给徐泊丽,一五一十的说出他的病情,独独隐瞒了他们的关系——那是她仅存的,自欺欺人。
徐泊丽的反应同任何一个母亲一样,难以置信,失声痛哭,那个声音仿佛忽然间苍老了十岁,却一直喃喃的说:”他一定去找她了……一定是的。”
五小时后,失踪了三天的乔远川终于给她打电话,云淡风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荟文,你愿意去欧洲吗?”
那一刻,担心,委屈,焦虑同时哽咽在喉间,她哭得说不出话来。
电话那头乔远川叹了口气。“别哭了,我没事。”
她拼命点头,却又想起来他是看不到的,气息平复良久,才断断续续地说出来,“我愿意。”
最后的三个月,林荟文每天拉开窗帘,都看的见阿尔卑斯山顶的积雪,乳霜一样的白色,令她想起小时候吃过的雪糕。那时她舍不得吃,就拿在手里,结果雪糕竟慢慢融化了,最后一滴都没留下。她大哭,家里的大人却都笑起来。觉得这小姑娘这样傻。
她将这个故事讲给乔远川听,他亦觉得有趣,嘴角微弯,低低地说,“从小你就这样傻。”
林荟文为他倒水,一声切开了他的腹腔,却因扩散太快,又匆匆缝上了。他躺在床上,瘦的愈发厉害,能让他笑,他觉得高兴。
大约是又发作了,她看到他额上的汗和隐忍的表情。不自觉地将手伸进枕头下,似乎要抓住那里的床单。
林荟文不愿多看,叫来护士,多给他一些镇定剂。
他的痛苦舒缓了些,皱着眉头,深深地睡去了。她小心翼翼地将他的手抽出来,想要塞进被子里,却意外的带出一张纸。
那是张很破烂的纸,曾经被人撕得很碎很碎。此刻又被粘起来,大约是一些碎片找不到了,零零落落,始终缺了三分之一的样子。
上边的字迹却是乔远川的。
他写的寥寥草草,她只看到第一行的中央,三个有些张牙舞爪的字,检讨书。
她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直到最后一行,“糖糖,谁给你出的缺的主意啊,我写不出来知道不?你再生气,我可真没辙啊!”
落款是乔远川,时间是五年前。
林荟文微笑,直到笑出了眼泪,看着乔远川林廓分明的侧脸,喃喃地说:“原来你以前这么幼稚。”然后重新将那张纸塞回他的枕头下边,不让他知道自己曾经看过。
乔远川醒来后,精神好了徐许多。
他让她打开病床边的抽屉,指着里面的 一沓文件说,“那是给你的。”
林荟文疑惑的打开,是一份股份证书,他将自己名下,公司里一半的股份留给她,一并转让的,似乎还有房子,还有许多东西。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不要这样看着我,荟文。”他吃力地说,“我知道你不稀罕这些,可是抱歉,我只能给你这些。”
他顿了顿,“我很感激你,却不知道怎么回报。请你收下……这样我走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愧疚。你还很年轻,有了这些东西,人生的底气会足一些,可以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再去找一个爱你的人。”
她移开了目光,低低地说,“这些东西,你应该留给你最在意的人。”
他微笑起来:“糖糖她……并不缺这些。”
她终于忍不住,湿湿凉凉的液体肆无忌惮地划过脸颊,“乔远川,你说过,你会好好活下去的——我什么都不要,你要好起来啊!你要好起来啊!”
她扑在他的床边,哭的说不出话来,“你好起来了……才能和她在一起……”
他伸出手,一下一下地抚着她的头发,却只是微笑着不说话。
她继续说:“你跑去敦煌找她,你们只在一起待了两天……这怎么够呢?”
他眷恋而满足的笑,轻轻眯起眼睛,目光的尽头,仿佛看到了沙山起伏,驼铃轻响。而唐思晨的身影就在眼前。他又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他背着她,他们温柔地在校园的小径上亲吻。那种软软的感觉,此刻竟然这样清新……他唇角笑意更浓,“傻孩子,对我来说,够了。”
午后,阳光落进来,却因为肃静的病房而显得苍白。他依然抚慰着她的肩膀,尽管动作很轻很轻,可林荟文却不敢再哭,也不敢在再动。
很久很久以后,那只手终于不动了。无力的垂下来。
直到此刻,终于知道自己不必在怕惊醒他,她慢慢的直起身子,放声大哭。
两个星期后,林荟文回到文岛。
秋天的陵园,阳光淡薄如水。
她在这里遇到很多人,亲人,朋友,还有……唐思晨。她不由自主的想去观察那个女人,她站在最角落的地方,面无表情,因为衣服是黑色的,≮我们备用网址:≯脸色预防显得苍白。仿佛秋风一卷,就摇摇欲坠。
林荟文下意识地将手伸进口袋,那里有一张薄薄的纸,上边粘着很多胶带,触摸上去,有些硬硬的,滑滑的。
那是属于他们的东西。
她下定决心,往那个方向走去。
唐思晨见到她,只是点了点头。
秋风渐起,落叶飘扬到脚下,慢慢地打着旋儿。
林荟文听到唐思晨的声音,“他……走的时候,痛苦吗?”
“不。”她摇摇头,又加重口气,“一点也不。”
唐思晨望着她,唇角勾起,那一笑,仿佛是感激,却又哀凉的深入骨髓。
沉默了良久,林荟文的拇指和食指一直捏着那张纸,她鼓起勇气,低低地说。“唐思晨……”
唐思晨侧过头。
林荟文看着她的眼睛,也看到她轻轻颤抖的右臂,忽然想起来,她知道“订婚”的真像吗?知道乔远川的苦心吗?她知道乔远……至死都这样爱她吗?
远处徐泊原正陪着姐姐慢慢走过来,他第一眼便找到唐思晨,他的眼神悲凉,却又有难以自禁的关切。
而唐思晨,像是感应到了他的目光,微微抬起下颌,努力的露出一丝微笑,仿佛是让他放心。
林荟文默默地看着,他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吧,想乔远川希望的那样。
她倏然收回了手,掌心紧紧握着那张纸,有些生硬的对她说:“他希望你……能幸福。”
徐泊丽亲手将儿子的骨灰放下去,工作人员便要最后盖上那块大理石,林荟文快步走到她身边,低低地说:“伯母,请让我撒些花瓣,好吗?”
徐泊丽看着她,这是陪着儿子走过最后一段时间的女孩子啊……她凄然的笑了笑:“好。”
所有人都看着乔远川的未婚妻慢慢地蹲下去。
她将花瓣撒下,动作仔细轻柔,最有又将手心攥着的那张纸,不为人知地轻放在骨灰盒旁边。
站起来之前,宛如老朋友般,她在心里说,“你放心,她会过的很好,她不会回头——而我明白你的意思,最后一分神情的负担,我亦会替你掩盖起。”
我将终身用一种温柔的心情,来守口如瓶。
唇边的诗句,静止在这一刻,淡漠时光中。
番外三 起点与重点之间
“快来看啊,双胞胎哎!好可爱!”
“啊啊啊啊,还是一男一女耶,怎么这么可爱?”
年轻的妈妈仿佛习惯因为这一双儿女带来的注目,至善善意地对那两个小姑娘微笑了一下,又蹲下身子,将儿子踢开的毯子重又盖上。
包里的电话响了,她将自己手里的婴儿也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