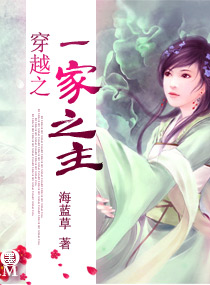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褪俏颐堑恼庖淮颐堑南乱淮R蕴ㄍ迦丝诘囊话胛及桑残砩俚愣闼且磺蛉撕昧恕U馐侨泄丝诘囊话偎氖种蛔笥摇5钦饬酱娜瞬荒芏家黄鹚阕饕欢眩蛭弦淮乱淮行┎煌I弦淮褪俏业恼庖淮缒暝冉锨罾У娜兆樱淮右痪牌摺鹉甏笃诳迹ㄍ宓木媒ソヌ嵘谀歉鍪贝錾哪昵嵋槐玻恢揽嗳兆邮窃趺垂模蘼凼蔷窕故俏镏实纳睿菀装寻惨菹硎苁游比唬遣⒎切以恕K堑谋г棺匀灰任颐钦庖淮嘈U馐撬悄俏灏偻蛉丝谥鞴鄯矫娴奈侍狻A硗猓颐钦庖淮诔沙さ乃暝轮校淙灰灿衅浼枘眩欢筇迳现灰Γ喽嗌偕僮苡惺栈瘢舜酥湟残碛行┎罹啵淇盏牡股偌5窍乱淮哪昵崛司筒煌耍芏嗳舜城俺蹋吮匦璧呐Γ挂吭似庠谖颐堑蹦晔遣惶嵯氲降氖隆N颐强丛似呛酶辉趺春玫牟畋穑怯谢蚴敲挥械牟畋稹U馐强凸刍肪车奈侍狻�
因此,想要在这个生存的世界上,有个小小的位置,大体上也不难,看来这个道理很合理,但是,在百年来的中国,却真是稀罕。在台湾的我的这一代,却遇到了。我们姑且认定这样的人有五百万。那就是全中国十四亿人口的二百八十分之一了。
跟同侪相比,还能找到一些条件,比如说,我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谁都可以对这个说法有其自己的解读,我的解读是,在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战乱、流离、匮乏、疫病,等等,时时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我们的上一代为我们挡住了这些严酷的试炼。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最痛苦的日子,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升平,即使在台湾风雨飘摇,面对中共大军,眼看就要失守之际,我们都还是懵懵懂懂,照吃照睡也照玩。把这类条件也算进去,我们这样的一代的这种人,应该是数百分之一的中国人吧?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时代基因,白白趟上的。对于生命,我们要是说感激,那是真话。
所以,纵使难免有些挫折,面对着百年来的大时代,就太微不足道了。但是这却是晚年的觉悟,在当时当下,也有许多的痛不欲生跟乐不可支。现在回头看看,一介微命,的确是太大惊小怪了。
要是能做到大怪大惊,小怪小惊,不怪不惊,甚而不怪却惊,有怪不惊,形形色色,各得其等次,他们也许蛮伟大的,但是太深奥,我不懂。
我们家是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却也充满了悲欢离合,我静静地,在不会发言也没有发言权的岁月里,静静地看、听、想。然后,随着一年年长大,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也都一件件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到老了的时候,居然又一件件地出现眼前,原先亮丽的色彩黯淡了许多,大多斑斑驳驳的,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只是残片,反倒更耐寻思,让人想起那些再也没机会见到的大部分。
有人说生命到了只会回忆,就没有什么展望可言,这大概指的是人已没什么用处,可是为人而无用的感觉真不错,人也只有活到相当岁数了,才享受得到这样没用的滋味儿。
文学作者以小人物小事件来写作,思想家则以想不通说不通的问题来思想,总归到了最后,用处难见,就出现了“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是过程就是目的”,糊里糊涂的。
我好像也只能说同样的话。
在大陆版的本书出版之前偶得上面的几句话,用来接在台版的短诗代序之后,也是序。
第一章 出生前后
引子
我的父亲马廷英博士。百余年前,从一个虎狼出没之地不告而别,到后来成为名闻国际的地质学者。
金州虎狼与小鬼
十六年前,作家故友陈恒嘉请我们夫妻俩南下,参加他们府上陈老先生八十五岁寿辰,令人难忘。就在彰化乡下老先生家的院子里,四围尽是水田,天光云影之间,摆上几张大圆桌,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坐得满满,煞是热闹。现场六七十人当中,只有长孙陈升的几位乐团成员跟我们俩不是他们的家人,不免有点感慨。
我们家是对日抗战胜利之后来台的,人丁乍薄,不必三代以上,便是父母之所经所历,知道的也十分有限。就是那么一鳞半爪,也多半是从父执长辈或是父亲学生的口中间接得知,有的却是从他人发表的文章中读到的,自两岸开放之后,又从大陆方面补充了几星几点,怎么说也谈不上完整。许多人能为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曾祖父母写上好多来历,我就难免惭愧。最近几年,还流行寻根修谱,但我们这样的人家,依然无头无绪。每个大年三十我们也会凑合着祭祖,便以红纸并排写上“辽东马氏苏州陶氏列祖列宗神主”,上供上香,简单处理。前几年曾经到父亲马廷英博士的出生地大连外围的金州,寻访他的出生地三十里堡(堡字读如“铺”)的马家屯,但早已沧海桑田不见踪影,其他种种更无从追寻。
父亲在家名雪峰,以廷英为号,以后就以号代名了。那个年代为自己另取一名,十分流行,这个后来的名号,有何来历,我不得而知,只是常常纳闷,家里给取的名字也不是阿猫阿狗,看着也还体面,干嘛要改?是否另有隐情?但答案已经在天上了。
父亲十几岁就离家出走,这样的行为可不寻常,算算应在百年以前了。今天,从金州三十里堡直放大连市区,一拐弯就能上高速公路,四十分钟到达,非常快捷便利。百年前可不一样,那是个虎狼出没的荒山野外,连到天涯海角,所谓走出去,应该说的是去大连吧?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走”的?童年的时候,姑妈跟我们讲,父亲书读得好,十几岁就考上了“满洲国”留日的官费,于是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学成归国,从学生到学者,就是他八十年一辈子的生涯。
父亲不告而别之后,也许家里辗转知道了他在日本,真相如何我也不得而知,但过了大约一年,他从日本寄回家一张照片,年轻的父亲坐在一架英文打字机前,照片后面简单地写着:“眼前是一架只要想到了,字儿就会出来的机器。”据说照得相当神气。他刚去日本读的是东北仙台的高等师范,然后读同样位于仙台的东北帝大。他有打字机可用,应在高师阶段,时间当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一年之久不通音讯,还是长子,家里面也不着急,这个家,很奇怪。后来看他一生也没把家当回事,当真是承传有自。
父亲的信写得那么简短,也许是因为我们老家上二三代没几个人能认字的。爷爷让父亲上学,无非只巴望他将来能记个账就很好了,父亲总是一边在野地里放猪,一边读书,看看书,看看猪,就觉得不该老死是乡,十分合情合理。大陆的网站上说他出身于小地主,却没说是野地里放猪的小地主。
他读书用功,又聪明过人,在金州中学时代就表现优异,家里弟弟妹妹的文具都不用花钱再买,只用这位长兄的奖品就足够了,这是姑妈跟我说的,我信。
爷爷看了看他那张打字机前的照相,只说了一句:
“日本有这么样的机器,该是个好地方,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吧。”
还能怎么样?父亲就这么样地留在日本,将近二十年之久,并且永远也没有再回家乡,我没听他说过爷爷奶奶的寿数,大概什么时候辞世他也不太清楚,姑妈也没提过,这也算是家风。
对于爷爷,我知道得当然更少。从前的身份证上有祖父母栏,有马德芳这么一个名字,祖母是什么氏,我也记不清楚。后来的身份证上祖父母这一栏也没了,我的祖父母从此也没了踪影。对于过去,只有在父亲的病榻前听他说了一点儿,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又跟姑妈通越洋电话,问了一点儿。
父亲是十四岁从金州中学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国中”,没有证据显示他在东北上了高中,从十四到二十七岁,中间哪些年在东北故乡?哪些年在日本?无从得知。只有二十七岁那年他高师毕业,是可以从许多文件中证实的,也可以证实他二十九岁就已经从仙台东北帝大毕业了,但得到博士学位时已经三十七岁,从研究所读到博士足足用去了八年,那么他在三十七岁前都在读书,之后都在教书、做研究到去世。
依姑妈所言,他十五岁去日本,但他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当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姑妈还未出生,容或不准。因为考取公费留学,看来不会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除非他聪明得要命。我猜他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家里要他结婚,他就私下考上了公费溜了。依我看,父亲的中文表达应该比他的日文差一点,虽然他的中文有点古色古香。那么早就出国闯前程的人,要以什么语言为母语,是个问题,至于他自我认同是哪一国的人,依我看,他嘴上从不说,却非常爱国。
我爷爷十六岁就当家了,原先是个石匠,先是做打石粗工,姑妈跟我在越洋电话里讲,爷爷少了一只眼睛,会不会是炸石打坏的?姑妈没说。后来因为能雕石,就成了雕石师傅,姑妈说他会雕石狮子,可见有点美术的天分,但也仅止于细工石匠,不像齐白石,从粗木工而细木工而画画、写字、作诗文成了大师。百年前的东北,也没有提拔齐白石的王湘绮(王辏г耍┠茄娜宋铩�
似乎家里的人口不少,生活得很不容易。而我姑妈生下来的时候,作为长兄的父亲,已经在日本五六年了,一老大一老幺,父亲排行最长,两人相差二十岁。算来他们兄妹首次见面时,父亲已经四十上下,姑妈对父亲的了解不会多,她听到的兄长也多过她见到的兄长。
我的学长,担任过“国立艺专”校长的王铭显教授,也曾留日,他念的是筑波大学,此校的前身,便是日本高等师范。先父病重,住在台大医院,他以校友身份前来探视,还带了高师的毕业纪念册,里头就有父亲的名字。这就证实了父亲最早的时候是读高等师范的,这么算算,父亲读高等师范时,应该就在二十岁左右。
这位年轻的东北青年,在去日本之前,交了个好朋友,年纪比他大上许多,有三十多岁,姓甚名谁?有什么背景?后来也没听父亲说起,只是邀他同去了日本。年轻的父亲专心读书,他就给父亲做饭吃,也许还帮忙干点别的事。其实父亲在吃的方面相当马虎,这位“厨师”的手艺纵使真有,大概也无从施展。后来他这位年长的老友在日本去世,也是父亲为他办完了丧事,老人家对我的说法是:“你爸爸就把他给埋了!”小时候我还以为是父亲亲手挖的坟呢。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可以推测的是,当年日本政府给的官费一定不少,还能养一个厨子。另外,我想父亲应当再也没有余钱汇给老家吧?由此也看得出父亲年少时就不平常,也不顾家。
不仅父亲年少就有单身远渡重洋的气魄,年幼的父亲也不同凡响。
这个故事倒是父亲亲自跟我说的。
在父亲大约只有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失踪了。
在那样的乡下,小孩子不见了,大家不会马上知道,因为随处都可以乱跑,到了天黑不见人,大人才开始慢慢儿着急,到处叫唤也没回应,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手电筒,大家打着火把找这个孩子,却一点影子都没发现。
老人家就一直操心到了天亮。
百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