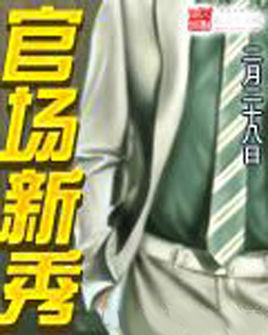首席外交官-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就算是这个掌舵人昏庸无能,那取代他的人也必然不会是其它船上上来的人,而极有可能是最底层的那些摇船桨的那些个劳苦大众,他们不会认为这个船有多破多旧,在他们的意识里,这条船就应该如此,而他们作为新任掌舵人的任务,无疑是让这艘船继续逆历史潮流而行,其结果也很明朗,如果没有外来的惊涛骇浪或是别的船只撞击,不管掌舵的人强悍还是懦弱,这艘船仍然会继续航行下去,这的确是一个国家的病态,但这个病态却难以以个人病症具体化,因为其治疗方法不是以外用药物抑制,而是在保留病态的中心的同时,自动将坏死部位进行更新,整个船上最高权力的新陈代谢秉承了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特色——自给自足。
更何况,如果马嘎尔尼在京城多逗留些时日,跟他口中的“中华帝国”的公务员们交流交流国际经验和心得,很快就能发现,这艘**的掌舵者虽然是名义上说一不二的最高决策人,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并没有一言堂的权力,或者可以说是不敢一言堂,因为他的水手们可以像马嘎尔尼看到的那样卑躬屈膝,以至于被这位异国使者认为是毫无尊严,但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自主选择给不给他们的“船长”面子——在两边护航的可以义正言辞地表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舱内办事的也可以毫不客气地据“礼”力争,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前仆后继的状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这些“水手”们管得越宽,甚至连“船长”早饭吃了几粒米,从卧室到办公室应该走几步,都上升到了国家大事的范畴,要讨论决定,而且一旦决定出来,作为“船长”还必须照着执行。
要是“船长”愣是不执行,甚至为了耳根子清静把这些倒霉的“水手”给扔到海里喂鲨鱼,当然原则上说也没什么不行,但是纵观“中华帝国”这条大船几千年延传下来的“航海日志”可以发现,能做出这样“壮举”的人实在不多,而且这样做的人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英明神武如唐太宗为了不被魏征批评也只能活活闷死自己的猎鹰,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结果了这个爱挑刺儿的,可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千古第一贤德的长孙皇后,硬是把这事给化解了。
最初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文官治国,是为了控制武人的野心,防止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发生在他的后代子孙身上,出于社会责任考虑也是预防五代十国,各镇割据的历史重演。武官的确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群体难以对付的群体,稍有点不顺心立马闹出点事端来让上面也不顺心,没脑子的揭竿而起,占个山头为王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有些智商的会借助地理优势拉帮结派甚至礼通外国,伺机而动,历朝历代虽然也采取了一些诸如使其家眷留守京师的做法来牵制武官的行动,但这不过就是皇帝自欺欺人的把戏,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要有心造反的,谁还能在乎自己的家室妻儿,朝廷要是把他的老婆孩子杀了,他就更加有继续作乱的理由——上头不义,休怪他不仁。
相比之下,将手无缚鸡之力,又只热衷于动口而耻于动手的文官阶层充当这个国家的顶梁柱,其安全性能的确提高了许多,但是当皇帝的未必就会觉得这样有多舒服,诸多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这个团体只能被使用不能被征服,这些人办事不是受制于皇帝的个人魅力更加不是受制于对朝廷的感恩戴德,而是遵从着孔子、孟子的礼数尊卑,你皇帝遵从孔孟之道,他们挺你,为你出生入死,肝脑涂地眼皮都不带动一下,要是碰上个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的,他们就会开始对你实行围攻政策,当然他们不会造反,因为孔孟告诉他们要忠君爱国,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特有的办法,比方说无孔不入的禁言战略,只要你不聋,大概是受不了一天十二个时辰不同的声音重复着同样的话。
而比武官或是藩王的造反更胜一筹的是,这些人往往可以在道义上占有主动权,中国自古讲究的是“礼法”——礼为先,然后才轮到律法的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对中国的律法自然可以拥有最终解释权,但是“礼”就不一样了,这不是哪朝哪代定下来的,而是以西周宗法制度和礼教为蓝本,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多位“高级技工”加以改造升级最终成型的,其最终的解释权自然自能归于儒学经典,若要把这个权力下放到个人的话,日理万机的天子肯定是与这项权利无缘,而从小就熟背四书五经,立志成为“儒学经典明珠点读机”的文官集团的成员们却绝对当之无愧。
所以,无论是在后世人的眼中还是当时天下百姓的眼中,文官集团所代表的就是绝对的真理和正义,而皇帝作为一个个体,他可以一人之力和一个人相抗争,甚至可以和国家机器相抗争,但若要和公理相抗争,的确也是力不从心。
因此,自秦始皇一统六国首先给“中华帝国”这艘**的船长套上“皇帝”的名头以来;这艘船上的船长或独当一面或共同执政,林林总总有一百二十几号人,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人战胜过外敌和心怀鬼胎的藩王,有很多人摧毁过宦官集团,也有很多人有效操纵了豪族门阀和外戚,但是却无一人可以战胜或者操控文官集团,甚至都不能表现出自己对这些人有任何不满情绪,被训了还要去亲自去低头认错,把人家给哄好了。
若是不想这么做那肯定免不了从此要被扣上一个昏庸的帽子在史书里被大书特书,这还不要紧,毕竟史书是留给后人看的,碰到前朝“正德船长”那样以娱乐至死为人生宗旨,生性豁达点的,懂得及时行乐的“船长”不会把这后人评说当一回事,但“天子失道”一事,后人能懂得的道理,天下百姓也能懂得,和天子血脉相连,但没能得到宝座的哥哥弟弟,和前朝的皇室后裔更是能敏锐地嗅出这其中的机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帝国哪个边边角角的头一炮一打,天下就不知道有多少城头要变换大王旗了。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8)
总体而言,套用沈哲曾经的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一种文体来表达就是“这些人你伤不起。”
按照常理而言,一个书生本应该是不足为惧的,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明确的告诉我们,团结才是力量,熟读经史子集的书生们当然也深知一个独木易断,人寡被欺的道理,更何况孔子、孟子这些至圣先师虽然教导过他们不可营私,但没人跟他们说过不许结党。
于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以及壮大自己的势力从而更有效地执行他们思想中的“大义”,更迅速地构建儒家社会的伟大目标,这些书生们自觉自愿地拉帮结派。
甚至还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的书生人数日益攀升,此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的自主行为,或以人生理想为界,或以地域为界,一些时候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与他们自幼年开始就承袭的教化大相径庭,但是文人是有辩才的,人家对这些行径解释为隐忍,当然“隐忍”或者“大义灭亲”这些词往往是留给最后在残酷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那个,至于失败的那方会有什么判词,这完全要看对手的心情,这么一看,好像是有点恶毒,与两汉时期的门阀外戚的斗争没什么区别。
但是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人的操守,并不仅仅是他们两袖清风或是自扫门厅之类的个人修养,而在于,即使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们虽然会毫不留情地给对手致命一击,但在成为胜利者的时候很少有落井下石之举。
整体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这些人之所以卷入到这些政治斗争中,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个人的名利或是满足自己的野心,而是在完成某种使命,沈哲常常想,大概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此时——正面临着时代变革的晚清,而这些道学先生们扮演的角色也是阻碍着民族进步,腐朽不堪的顽固派,但仍然要将他们称之为“清流”——这个颇具有莲花气质,完全找不出任何贬低含义的词汇。
当然如果文官集团仅仅是依靠着共同信仰,或是他们彼此之间对对方的敬重,很显然不能让他们产生如此可以与黄泉抗衡千年的凝聚力,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个世界上到目前为止,真正不需要一个最高权威管理,意依靠人民自觉自主运作的社会形式只有两个——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些文人士大夫的眼中,前者社会形势下的居民不识荣耻,不知礼教,他们看不上,至于后者他们根本就没这概念。
因此,在他们的小团体中势必就也要出现一个挑头的权威,这些权威需要有背景家事,但并不是像三国时的袁绍、袁术兄弟俩一样凭着个四世三公的家底就可以的,在这些儒生的眼中,背景只能说明你的良好出身,但要当一把手,首先得在学识上做一番比量,由此产生的结果这是,这些挑头的人虽然也有被莫名其妙被推上这个位子的,但是绝少有什么都拿不出手的真正的庸才,就算是臭名昭著如南宋的大奸臣蔡京,人家至少也有一手可以和米芾等人比肩的好字。
这样一个集文坛泰山与政界北斗(后者在很多时候有一厢情愿之嫌)于一身的文官集团领军人物历朝历代都会存在,或在明处,或在暗处的区别而已。
在沈哲的印象里,晚清的相应人物应该属于历任三代帝师的翁家。但自从得知在这个次元中,历代大清皇帝的老师里都没有姓翁的人物,他就开始留意观察寻找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翁氏一族在这个世界里的替身。
自从得知自己是处在与原来完全不同的世界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沈哲也逐渐有意无意地留心周围与他记忆中的许多不同之处。渐渐地也被他掌握了一些门道,虽然这个次元和沈哲本来的那个次元的相似程度已经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程度,但毕竟仍然是两个不同的平行世界,在许多细节方面还是有出入的,好在沈哲在不知情的时候话不多,偶尔的几次议古论今,也都碰巧地没有涉及到这些细枝末节,才一直以来没有露出过破绽。
不过,虽然仅仅是细节不同,但众所周知亚马逊的一只蝴蝶拍打一下翅膀也可以给千里之外的某个倒霉地方带来一场飓风,这两个世界之所以还能在数十万年的岁月长河中化解这些细节带来的影响,发展出两段惊人雷同的历史,其关键就在于这些细节上的差异都可以进行等效替代,除了名字不同,人不同,但是造成的影响却都是一摸一样的。
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次元并没有翁同龢、翁存心这些人,但是必然会出现一个足矣取代起作用的人,来稳定秩序。
沈哲对于这个人或者说是这个家族虽然也没有仔细找过,但是却在时时留心着,但照现在看来,似乎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照着刚才借着极度有限的时间里跟钱喜打听出来的那点信息来看,眼前这位对自己有点吹胡子瞪眼的荀大人就是这个时空的翁氏一族无疑。
荀大人者,名荀同祥,还是七十多年前大清最鼎盛的时期,由当时一事暮年的乾隆皇帝亲自赐予的名字,圣上亲自赐名,更何况还是赐予一个汉人,即便是在这个次元的大清的历史都是寥寥无几,足见荀家之举�